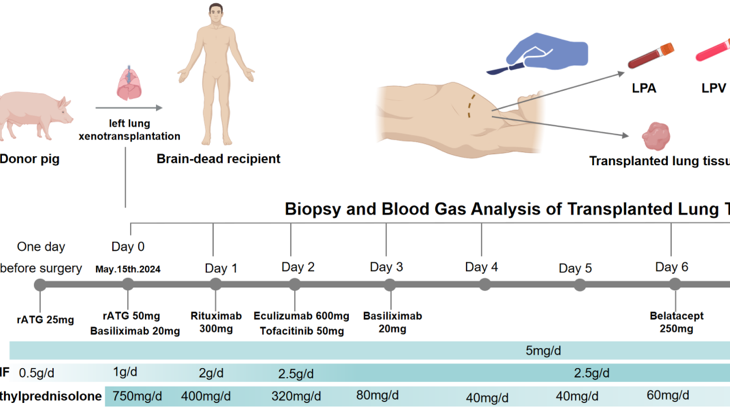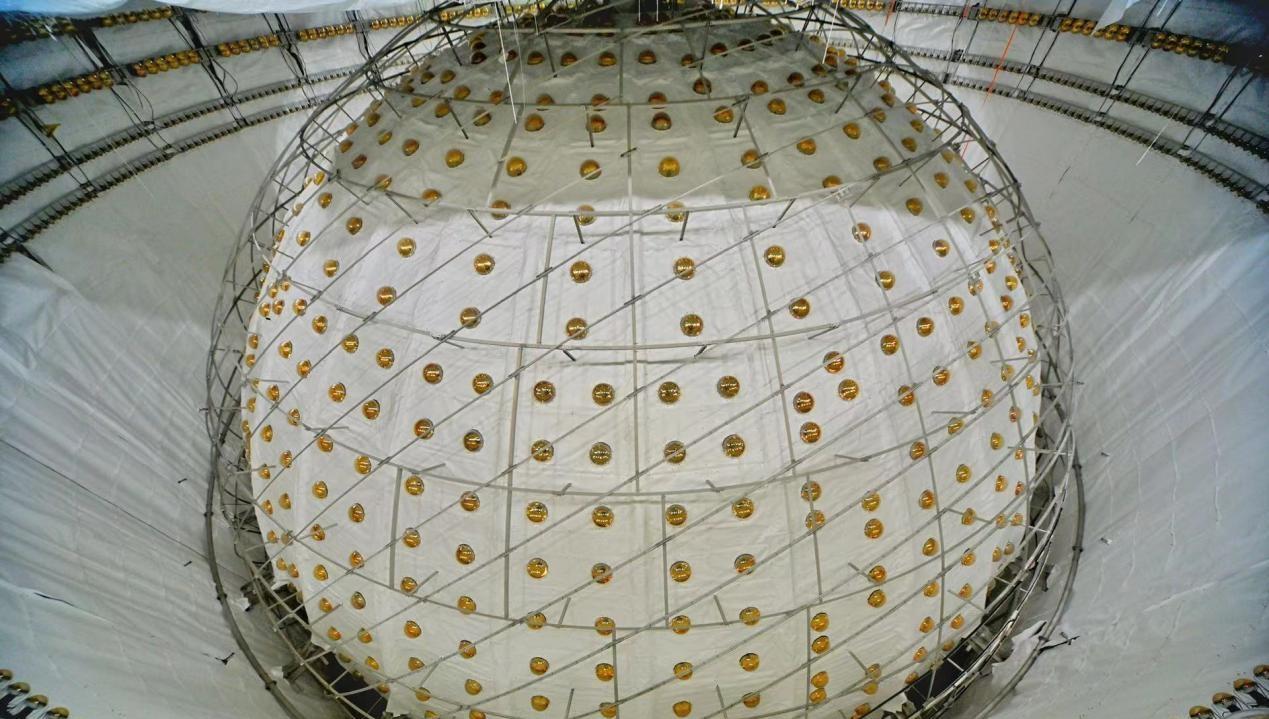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陈汝健
站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石门寨镇政府办公楼上东望,近千亩采矿遗留矿坑如大地的伤疤般裸露田间。深坑里蓝色的水面平静如镜,浅坑中停置的采矿机械锈迹斑斑,与周边青翠的玉米地形成刺眼对比——这是露天开采留给这座滨海之城的典型“伤痕”。
矿产资源丰富的河北秦皇岛,全市持证矿山企业115家,其中30家曾进行露天开采,仅海港区未修复矿坑及周边生态面积就达4160多亩,多数未有效治理,持续影响周边环境及地下水。
记者调研发现,这些露天矿山关闭后遗留的生态创伤,广泛存在于我国东部矿产资源县市,如承德滦平、邯郸武安等地,形成有主矿山“停而不修”,无主矿山“财政难扛”现象。滞后的生态修复,让本就脆弱的矿区生态环境变得日益凸显。

关停矿山,莫闭修复之门
“这些多年前嗑石子形成的矿坑,最深处达80米,几乎都跟地下水源打透了。”秦皇岛市石门寨镇北林子村党支部书记顾立怀面对连片的矿坑忧心忡忡。这些采矿遗迹占用的几乎都是一般耕地,不能随意填埋,否则影响饮水安全,却又无力修复,成为悬在村民心头的生态隐患。
顾立怀介绍,矿山虽关停多年,企业每年仍向村里缴纳6万元承包费,但生态修复责任却束之高阁。这片近千亩的矿坑,还涉及周边高井、南关等多个村。在秦皇岛市海港区,像这样的采矿遗留大坑还有多个,如该区的弧山峪、半壁山等村。
百公里外,迁安市隆宇工贸有限责任公司黑龙山铁矿,一个深达70多米、面积700多亩的露天矿坑已静待修复多年。该矿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2020年转为地下开采,地面矿坑因处于塌陷区,至今未启动修复。
迁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王大江透露,该市除南山铁矿等4家生产矿山企业外,还有28家停产矿山企业遗留露天矿坑,主要分布在蔡园、马兰庄等乡镇,几乎都陷入“停而不修”的困局。
责任主体灭失与资金断流形成双重枷锁。秦皇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调研员王建辉直言,这些矿坑都是持证矿山企业在过去监管不严时所为,应是谁破坏谁修复。但现实是,关闭矿企多数断了资金来源,将矿坑修复责任悬置起来。
王建辉还认为,目前资金是生态修复中的难题之一。为减少资金投入,秦皇岛的历史遗留矿山主要靠自然恢复为主。
地方财政亦难以扛起修复重担。秦皇岛市海港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殷亮介绍,2015年区划调整时,该区接收临县60家矿山企业及2840余万元生态修复保证金和利息。面对众多待修复矿山生态,他坦言:“矿坑恢复成本太高,施工工期也太长,目前也只能是回填。”
殷亮介绍,他们曾协调企业尝试利用粉煤灰填埋矿坑,记者在该区石门寨镇北斜村的矿坑填埋现场看到,目前这个填埋项目仍在进行中。但这种简单回填方式在相邻不远的北林子村却行不通——因矿坑与地下水系相通,任何填埋都可能污染水源。
对于历史遗留和关闭矿山的生态修复,多数地方相关部门均表示“财政难扛”,这正是矿区地貌难以恢复的关键原因。
在全国范围内,“十四五”期间虽完成矿山生态修复120万亩,但历史欠账规模仍触目惊心——仅山东省就“贡献”了15.3万亩废弃矿山。这些数据背后,是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的广泛性与修复工作的艰巨性。

为矿山生态修复找出路
当多数地区还在为修复资金发愁时,河北徐水区“以资源养修复”的做法似乎让人眼前一亮。京昆高速河北徐水孟村段向西,象山生态修复项目工地机械轰鸣。钩机挥动铁臂,翻斗车往来穿梭,这里正在抚平一座5085亩的“白茬山”创伤。
负责这一项目的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经济开发区副主任刘珞告诉记者,这个总投资4.68亿元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项目,包括高陡坡、采坑及周边未利用地的生态修复,其创新点在于土石方拍卖变现修复资金。
刘珞介绍,徐水区将修复过程产生的948万立方米土石方拍卖给石材加工企业,换来4.37亿元反哺生态修复。在2020年11月签约时,刘珞所在单位尽管与施工单位约定28个月后的竣工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协商,但时至今日,该项目仍因修复资金等原因致使工期一再延长。
放眼各地,以财政或专项资金支撑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较多。但修复方法不同,其修复成本与成效截然不同。
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另一场资源化利用的修复革命正在发生。该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级主任科员刘芳告诉记者,当地一个白茬山修复项目,抛弃了削坡造台的旧思路,采用挂网喷播技术直接贴合山势。这种方式不仅减少山体二次破坏,还节省了修复成本。
制度创新亦在加速。7月29日,湖南省自然资源厅正式印发《关于严守土石料利用政策底线 进一步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激励措施的实施细则》,直指土石料管理风险,严防“生态修复之名行非法采矿之实”。
河北省卢龙县的实践印证了转型潜力——该县一项近2000万元的历史遗留矿山修复项目中,有7至8个矿坑进行差异化治理。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三级主任科员告诉记者,矿坑周边有废料的就直接回填,不能回填的就转型利用或围挡。
产业融合正拓展修复的价值边界。7月24日,在2025年土壤与地下水风险防控与生态修复技术交流大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二级研究员张发旺就矿山生态修复绘制了“资源、经济、产业”三张蓝图。他认为矿山生态修复只有变成产业,形成新的“矿山”,才能可持续发展。
张发旺举例,传统酸性矿坑水治理成本高昂,若利用其特性制造成矿,如制取试剂或电池材料,就能将污染治理转化为产业。
对于绿色矿山生态修复,水利部牧区水利科学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珊丹则描绘出“生态+”的多元场景——露天矿山可采用“生态+农业+养殖”“生态+景观+文旅”模式,井工开采矿山适用“生态+仓储用地”,采空区则适合“工程修复+植被重建”或“生态修复+光伏产业”。在她看来,唯有构建起“生态修复+技术创新+产业融合+制度保障”的四位一体机制,矿山生态修复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推动矿山生态修复更科学
在以地质为“骨架”,水文为“脉络”的矿山生态修复中,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成效?水土修复领域专家共识明确:既要抓前端,治未病;更要抓末端,治已病。
在满城区李家佐村与玉山村之间,一片曾遭开采重创的白云岩山体群正经历一场改写开采方式的革命——“纵切变横切”。刘芳点破精髓:传统纵切形成高陡边坡,修复困难;而这种水平分层开采则使山体形成大平层,从源头减少修复压力。
纵切开采遗留的伤痕需要数十年修复,而横切模式直接将生态成本压缩在开采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这一开采模式可以由纵切直接变为横切、调整开采范围或合并整合后变为横切等多种方式。这一开采模式虽审批周期长,但是许多关停矿山企业仍在为此奔波,这已成为河北推进矿山“前端防控”的重要探索。
对于这一开采模式转型期的修复责任,河北省易县自然资源与规划局副局长徐士超认为,矿山生态修复不能搁置,纵使企业正在办理“纵切变横切”手续,仍需完成原开采许可范围内的生态修复任务,以防新批复范围不包含原区域。

在易县高村镇卓家庄村西南的一座山脚下,通过“削山腾地”新建起数栋石材加工厂房。该镇镇长高峰告诉记者,这种“挖山建厂”方式,既解决了企业占地问题,还节省了生态修复成本。
相关专家认为,矿山生态的源头防控仍需转变思路,从开采管控转向科学治理。在珊丹看来,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已不是点和线的问题,已经形成面和网的趋势。
在修复技术最前沿,一场水土重构系统治理正在西部矿区创造奇迹。“生态修复的实质是土壤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二级教授毕银丽道出技术核心。她的团队发明的“三层海绵土层重构技术”,在内蒙古准格尔矿将植被覆盖率从45%跃升至85%。
“底部隔水、中部涵水、表层种植,水分利用率提升30%。”毕银丽展示的监测数据令人振奋。这项技术已陕西、内蒙古等地矿区推广至40万亩,甚至在新疆红沙泉露天矿实现“当年成活、三年变绿”,突破干旱区修复禁区。随着土壤重构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矿山土壤重构已从1.0走向4.0时代。
土壤之下,水脉相连,水土治理亦在协同推进。面对34.2%地下水受污染的严峻现实,生态环境部土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熊燕娜疾呼:“地下水不能靠末端治理,必须源头防控。”
面对煤矸石填充污染地下水风险,相关专家呼吁攻关固废科学处置技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高级工程师何亚平则带来希望:“20469个自动监测站织就国家级地下水监测网,水质水温实时可知晓。”

新法新标构建起“制度约束+技术支撑”体系。2024年8月,《金属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等4项国标实施,首次对生产矿山明确“边开采、边修复”要求。新修订《矿产资源法》更专设“矿区生态修复”章节,系统性重构责任体系——法律的刚性约束正为技术落地铺平道路。
矿山复绿之路仍有资金之困、技术之难,但希望之光已在裂缝中透出——当“三层海绵土”在新疆戈壁催生绿意,当“纵切变横切”从源头抚平山体创伤,当20469个监测点紧盯地下水流向,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正步入科学化、产业化、智能化新纪元。那些静待修复的生态欠账,终将蜕变为生态与经济共生的新沃土。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