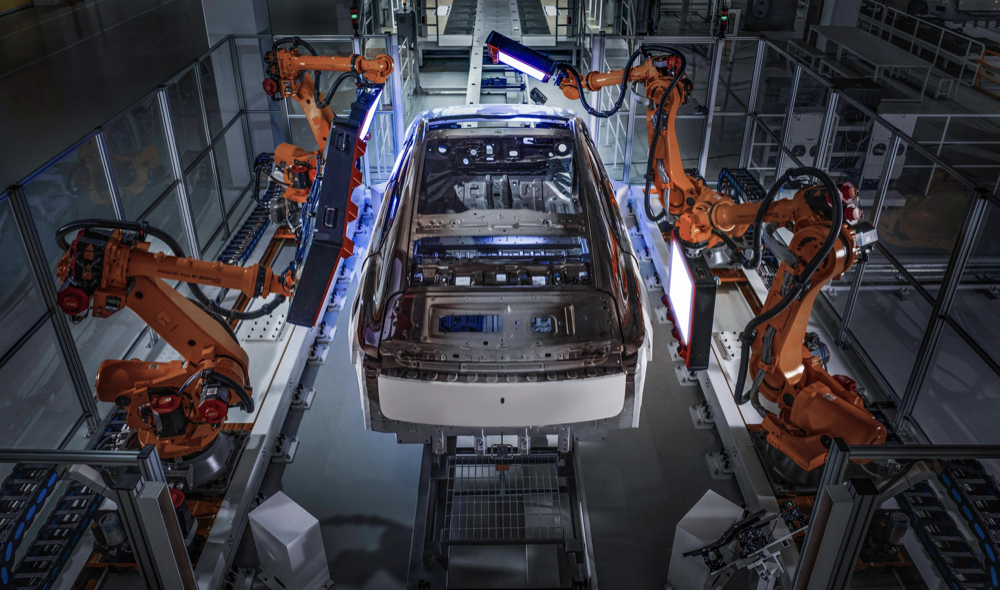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金凤
“嚓嚓,嚓嚓……”4月18日上午8:30,当晨光洒向南京云锦研究所(以下简称云锦研究所)的大花楼织机,丝线与织机的摩擦声再次响起。
拽花工潘德高坐在两人多高的织机上层,通过丝线的提拉、收放,提示他的搭档、织工闻万福何时织入纬线、妆金敷彩。丝线的尽头,闻万福端坐织机前,右手握着纹刀、飞梭,左手抓取金线和缠绕着五颜六色丝线的绒管,在“通经断纬”中,将画纸底本中的纹样活化为色彩绚丽的锦缎。
织机作画架、纤丝为画布、绒管似画笔,古老技艺映照千余年织造智慧,指尖拨动编织永不褪色的文明图腾。

寸锦寸金,两人协作每天仅织几厘米
走进南京云锦博物馆二楼展厅,4座于1982年投入使用的大花楼织机至今仍“吱吱作响”,一寸寸“吐出”光彩照人的云锦。
南京云锦因其材质使用“金纱翠羽”、色泽“灿若云霞”,有“锦中之冠”美名,因其用料考究、织造精细,亦有“寸锦寸金”之称。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云锦的工艺很复杂,如果要织一幅78厘米宽的锦缎,就要有1.1万根经线,再用不同色彩的纬线,在经线上穿梭。”南京云锦研究所技术部经理、南京云锦非遗传承人陈诚是个“织二代”,从小在机房长大,织机是他再熟悉不过的玩伴。自2009年进入云锦研究所工作后,学机械的陈诚已参与了不少织机的复原、改造,还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
“‘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技艺的关键和核心,要把图纸绘制成意匠图,它相当于编程,需要匠人将图案拆解到每一根不同颜色的经线和纬线上。”陈诚说。
在云锦研究所纺织品文物修复师侍康妮向记者展示的一幅图上,云锦纹样像十字绣一样被分解为若干个纵横交错的小格子,其间被不同颜色填充。
“我们会将纹样图拆解到每平方厘米,再将每平方厘米拆分成数百个小格子,每个小格子都由经纬线交织而成。”侍康妮说,接下来,挑花工会根据纹样每一纬的颜色顺序,用挑花钩依次把耳子线引入,制成花本。
把“花本”装在长5.6米、宽1.4米、高4米大花楼木织机上,匠人们便开始妆花了。“由于工艺复杂,即使在今天,两个工人每天工作8小时,也织不到10厘米。”陈诚说。

与古谋新,千余年织造智慧打造当代精致美学
历经1600余年工艺传承,如何让云锦织造的古老技艺迸发时代活力?陈诚和他的同事们将答案织进云锦的一丝一线中。
去年底,陈诚、侍康妮团队花了两年时间,为湖南博物院仿制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的陪葬品——绛紫绢地长寿绣丝绵袍。
绵袍的绒圈锦面料呈环状圈特点,是汉代织锦中的特殊品种。“由于文物年代久远,我们借助现代高清扫描设备,拍摄了许多显微细节图,以此分析绒圈锦的结构,发现它的经线很多、结构复杂,所以改进了织机,并用不同规格的鱼线,织成绒圈效果,待织完后抽出鱼线,得到圈状形状。”陈诚说。
传统技艺与西方艺术碰撞,也曾让东方美学闪耀西方时尚之都。2015年,云锦研究所26位设计师、4名织工耗时6个月创新技艺,首次采用“逐层异色”的染织方法,以70多种色彩的丝线,织出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作品在米兰世博会甫一亮相,惊艳世界。
以古为纲,与古谋新,与时代相向而行的云锦传承人们,眼下正让云锦从古时宫廷的御用品变为时下流行的日用品。行走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展区,云锦织造的山水画、风景画、花鸟画,形象逼真、色泽清雅。云锦丝巾、云锦坤包、云锦胸针、云锦礼服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好。
“我们结合当代人的审美,跟画家、装饰协会、学者合作,融入当代绘画元素和装饰风格。”陈诚说,除了构图,原材料的选择也更加多元、精细,他们也会将鸵鸟毛纺成线,将螺钿磨成粉裹在线上增加云锦光泽。
“我们希望在保护、传承云锦织造技艺的同时,面向时代、面向生活,结合新的科技手段,创新产品开发形式,让大家充分感受云锦独特的魅力。”陈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