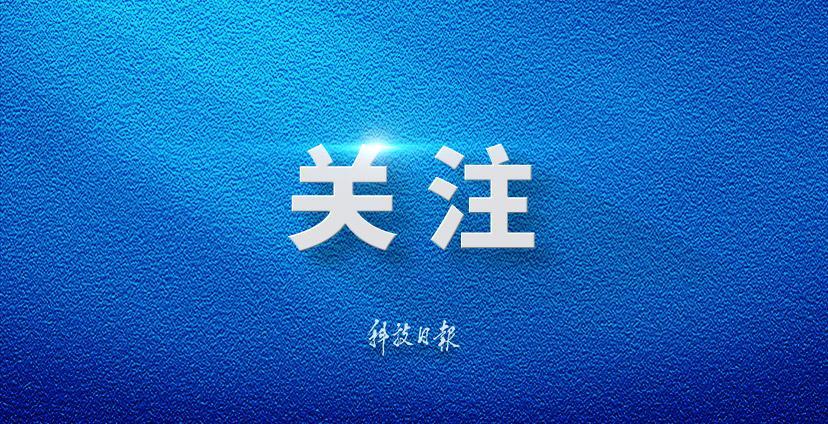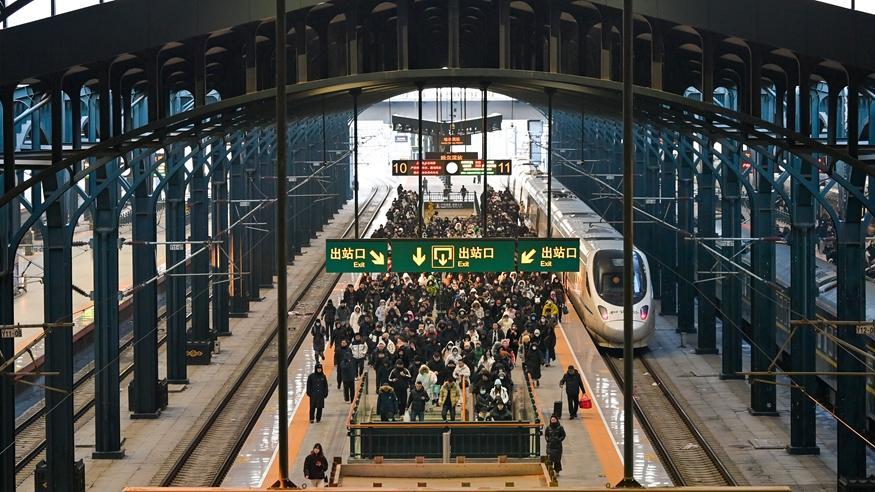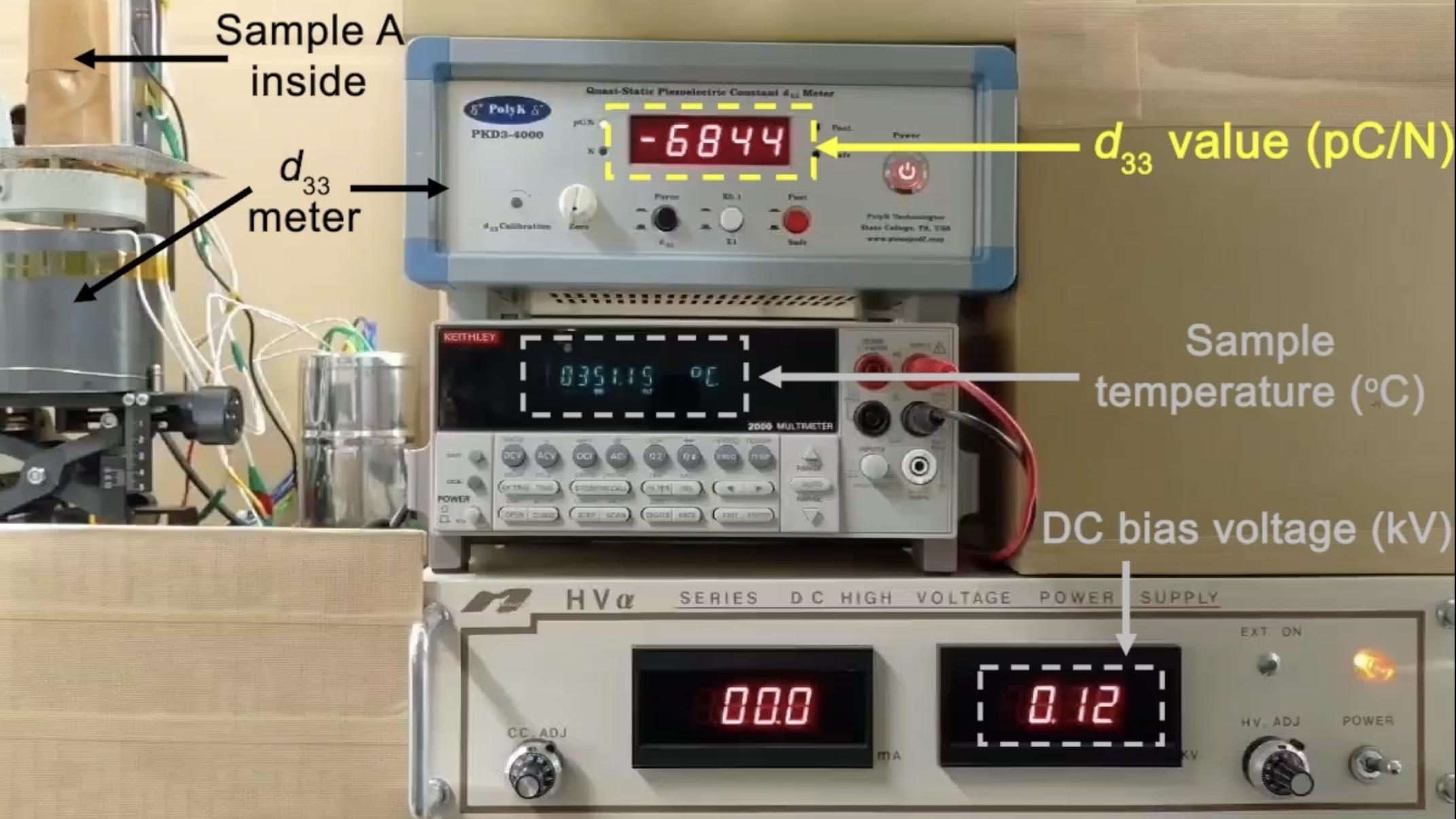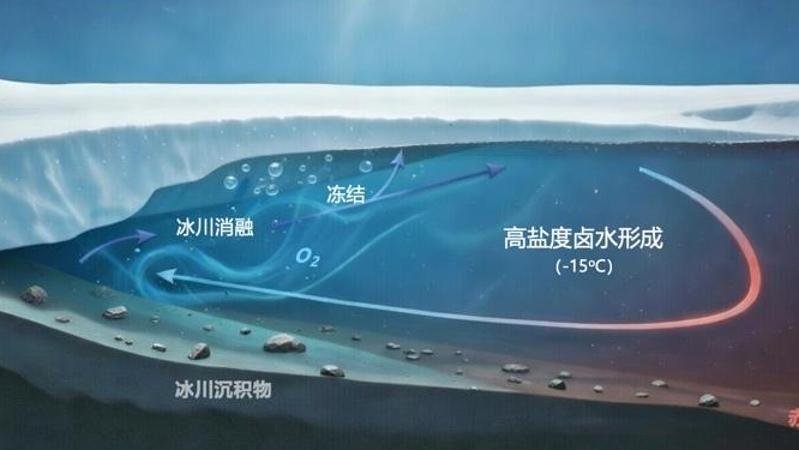科技日报实习记者 荆晓青
面对海洋,人们从未停止过探索。早在神农尝百草时,就对海洋药物有了记载;近年来,采用现代化学手段从海洋资源中获取小分子化合物,成为新药研发的重要方向。日前,第790次香山科学会议于北京香山召开,50余位专家围绕“海洋药物发展科学问题与技术创新”展开研讨。
大会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郝小江表示,根据《国际海洋法公约》,海洋生物资源谁采集研究谁受益,推动海洋生物医药发展,需要通过国家重大专项提供系统性、集中式支持,做好顶层设计,破除评价体系约束,从海洋技术、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协同努力,破解科学问题和技术瓶颈。
海洋资源潜力广阔
海洋生物医药是指以海洋资源为基础,开发生产和应用于维护人们健康的相关产品,包括食品、营养品、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医美产品等。近年来,科技进步为其创造了发展新机遇,其中,海洋中药、现代海洋药物、海洋生物医用材料等弥补了陆地药物和材料的不足。
“《中华海洋本草》中记载了我国海洋中药613味、含有海洋生物的中药方剂3100个,这展现出海洋中药对人类健康的重要作用。”大会执行主席、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教授杜冠华介绍,海洋中药的现代应用主要包括,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作为中药材应用于中医临床方剂、中医成药组分,作为食药物质应用于保健食品、药食同源食品开发等,还可应用于人体“健康-亚健康-疾病-康复”的全过程。
“对疾病机制的生物学认识是现代药物研发的主要驱动力,分子化学空间的可及性则是药物研发的物质基础。”大会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俞飚表示,采用现代化学手段从海洋资源中获取小分子化合物,是新药研发的重要方向。
治疗白血病的阿糖胞苷,抗菌药物头孢菌素,治疗肺结核的利福霉素,治疗流感病毒的卡拉胶……不同于陆地的环境和更高水平的多样性,海洋孕育了独特而丰富的分子空间,这赋予了海洋药物研发的独特潜力。经过长期努力,人们已经从海洋资源中发现了4万多种化合物。目前,全球已经有20余种海洋药物在世界各国实现临床应用,处于临床Ⅲ期的海洋候选药物有6个、Ⅱ期的有12个、Ⅰ期的有42个。
在海洋生物医用材料方面,多糖、胶原、蛋白质、纤维素等展现出优质性能,被广泛应用到促进伤口愈合、加快组织修复、跨血脑屏障、靶向和治疗肿瘤等疾病治疗场景中。其中,以海洋多糖制备的栓塞微球为例,既可以达到栓塞效果还可在人体内降解,在临床上展现出独特优势。与会专家表示,海洋生物来源的材料开发和应用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和转化过程,涉及获得材料、认识材料、材料产业化等环节,其终极目标是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多要素协同 助力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药物凭借高度结构的新颖性与多靶点调控优势,不仅为特定疾病提供了治疗药物,更在肿瘤治疗、重大疾病、罕见病等方面潜力巨大。然而,我国整体取得的成就还非常有限。
“以海洋中药为例,我们对海洋物质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当下,亟需从海洋中药提取物成分、药理作用以及采用现代药理学方法进行评价方面加强研究。”杜冠华说,海洋生物医药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海洋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需要以药性功效等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突破,带动海洋生物医药研发及产业化。
“限制海洋药物研发的瓶颈之一,是海洋生物产生的分子难获取,缺乏足够的量来进行药物研发。”俞飚解释说,海洋物质虽然众多,但与陆地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大的流动性,这导致获取困难。他建议,通过海洋分子的宏观发现技术、海洋分子的生物合成和化学合成技术等来解决海洋分子的可及性。
海洋分子的可及性也限制了海洋生物材料的研究。“海洋生物材料类型太多,研究人员很难针对一种材料深入到应用层面做极致研究;加之每种成分获取的量非常少,难以进行深加工。”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俊峰说,目前海洋生物材料还处于起步阶段,亟需回归动物本身的物质基础研究,厘清其构效关系以及其与机体的作用机制。
药物活性和评价策略也是一大难点。“海洋来源的化合物具有结构多样性和新颖性,这导致方法难测评;海洋中药则面临着传统方法难以体现药材差异的尴尬,例如,如牡蛎、贝壳目前以化学成分为分类,都被归类为碳酸钙,实际上二者在用药效果上表现不同。”杜冠华表示,无论是现代西药还是海洋中药的创新研究,都需要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围绕海洋药物的研发技术和特点,推动以创新作用机制和开拓治疗领域为主导的药物活性评价策略。
此外,人工智能正为海洋药物研发破局。
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贾彦兴提到,AI将加速化合物合成路线预测,在活性衍生物设计、发酵工艺优化等方面发挥作用。未来“化学合成—生物制造—AI融合”三位一体的研发模式,将为海洋药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根本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郑明月则表示,构建海洋天然产物专属数据库与AI工具,通过“AI预测—实验验证—临床评估”的闭环,将加速海洋药物从发现到应用的全链条创新。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