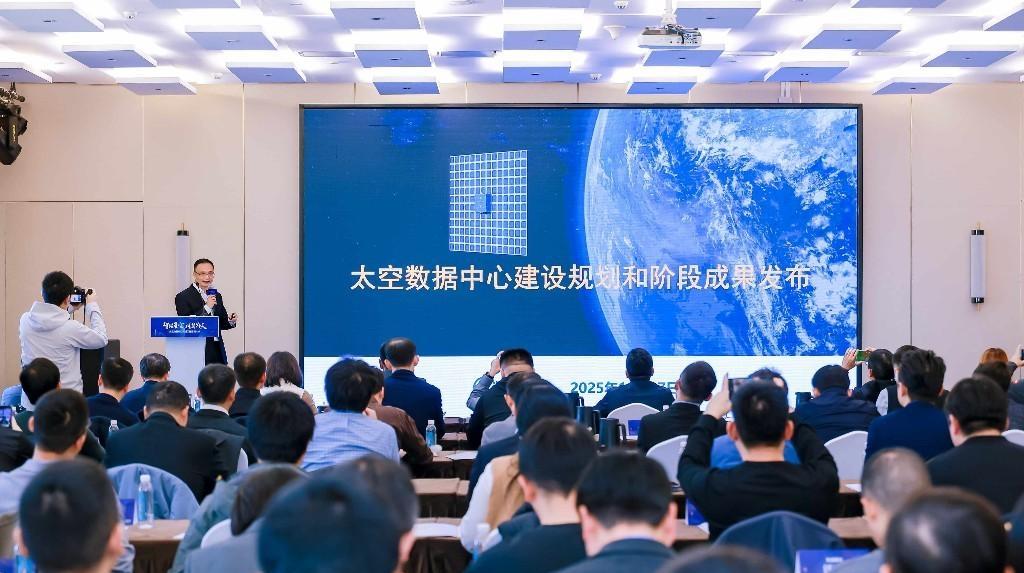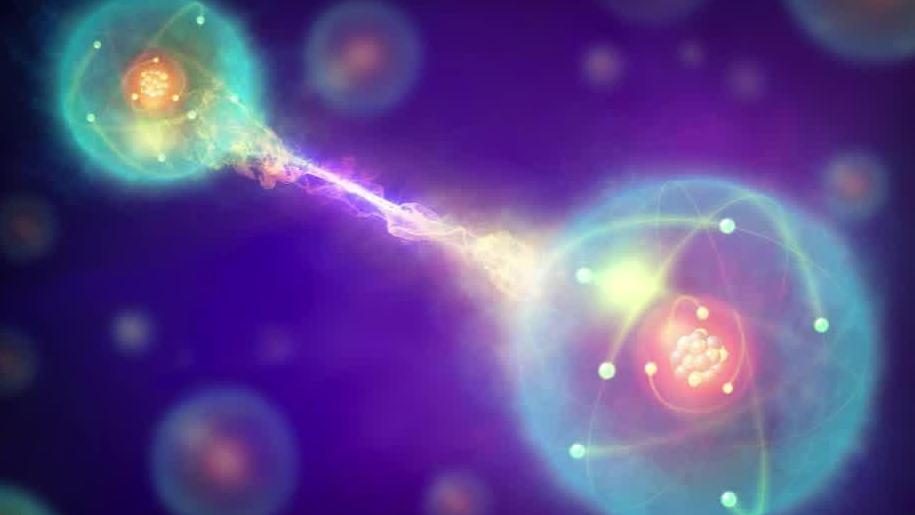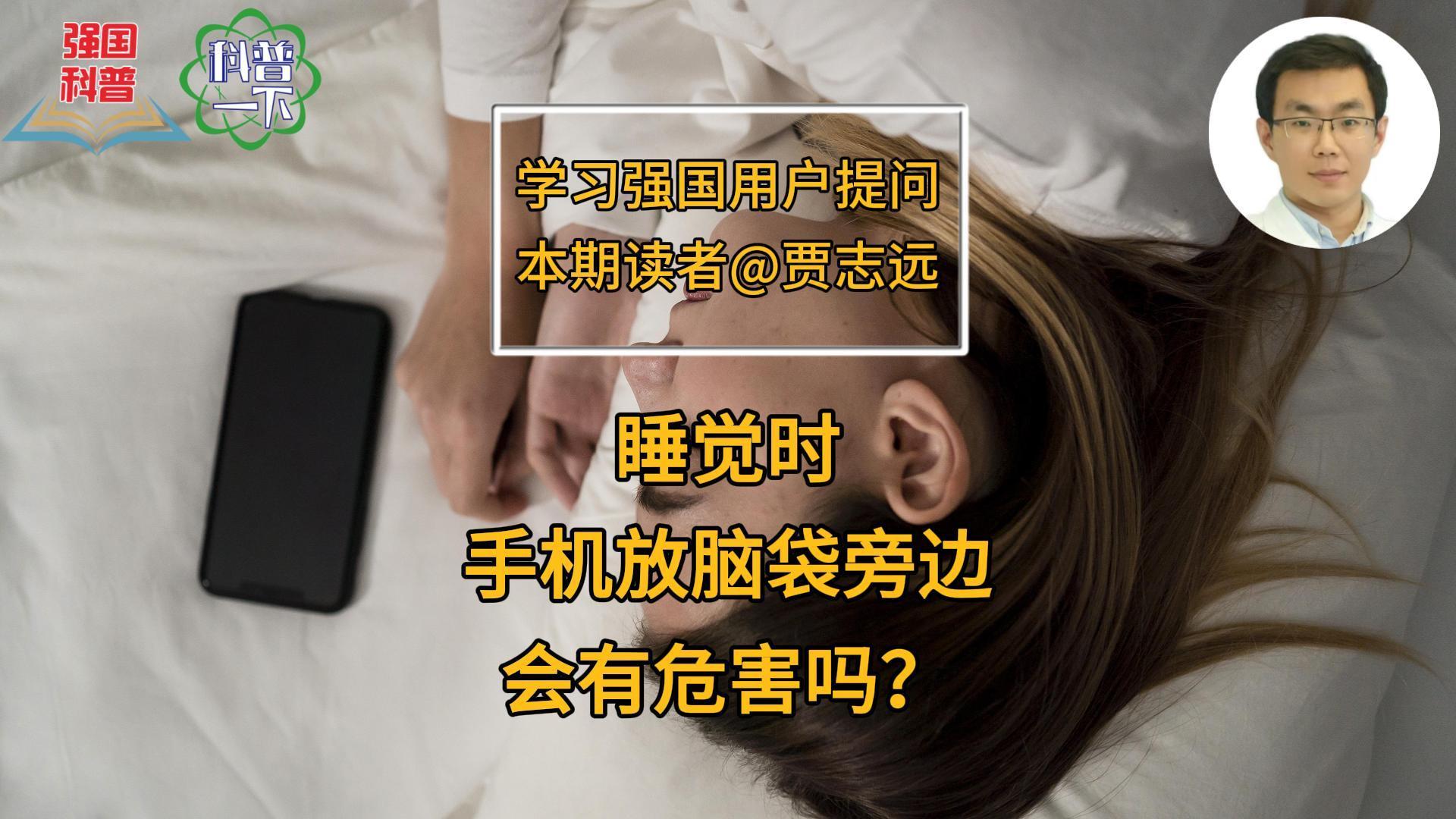◎张恒力 吴 圣
当我们站在科技飞速发展的21世纪,回溯19世纪英国烟囱林立的工业图景,那些在蒸汽与钢铁中沸腾的技术变革,恰似一面棱镜,既折射出工业文明的璀璨光芒,也映照着技术的暗影。在《工程帝国:19世纪英国技术文化史》一书中,作者将蒸汽动力、铁路、电报等技术嵌入社会文化语境,从多维视角揭示了这些技术与制度、观念、权力的复杂互动关系,反思了如何理解和解释技术的历史角色,并系统地展现出19世纪英国工程技术发展的全貌。
不同于“辉格史观”简化技术进步的线性逻辑是本书的一大特点。176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如同一只振翅的蝴蝶,从英国煤矿深处掀起了改变世界的风暴。这本书告诉我们,蒸汽文明的诞生绝非“天才发明家”的独角戏——威廉·西蒙金的高压蒸汽机试验、罗伯特·富尔顿的蒸汽船探索、亚瑟·伍尔夫的复合式蒸汽机改良……共同构成了技术共同体的协作史诗。当蒸汽动力从煤矿抽水机延伸至纺织机,当煤炭作为“太阳的储金券”打破生物能的千年桎梏,人类才第一次真正触摸到自然能量的脉搏,叩开了化石能源主导的文明新纪元。
火车的汽笛则奏响了社会变革的序章。1825年,来自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列车的轰鸣,不仅将人类速度提升至“1小时24公里”,更碾碎了农业文明的时空观。当布鲁内尔的宽轨铁路因成本让位于斯蒂芬森的标准轨,技术标准在铁轨延伸处编织起现代性的秩序之网。
批判性同样在书中得到体现。在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光晕下,19世纪的英国将技术奉为文明的图腾。但本书却揭开技术理性的面纱,让我们看见其背后的文化霸权逻辑。
当英国工程师在印度铺设铁路时,他们运来的不仅是蒸汽机车,更是格林威治时间的强制推行。在火车汽笛声中,时间认知得到了重构,这种“时间殖民”实质是以技术之名实施的文化斩首。而马克思笔下“机器革命”的双重性也在此尽显。所幸,当社会沉浸于“技术万能论”的迷狂时,文化界的反思已如晨钟敲响。华兹华斯在《序曲》中哀叹“铁路切开自然的胸膛”,约翰·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灯》中痛斥工业美学的贫瘠,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塑造了资本家葛擂硬,将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异化凝固为文学标本。这些浪漫主义的批判并非反对技术本身,而是警惕“效率至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吞噬。
此外,本书还关注了技术对于某些职业社会文化属性的重塑。例如,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程师还只是“拿扳手的匠人”,但铁路网如同魔法棒,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社会坐标。皇家学会向工程师敞开大门,《泰晤士报》为铁路庆典开辟专栏,工程师的肖像登上邮票与版画,成为“理性化身”与“进步图腾”。这种身份重构的背后,是工业资产阶级精心策划的“文化政变”——他们试图用“工程师精神”取代贵族的骑士精神,将技术精英塑造为新的文化霸权载体。当工程师从车间走向社会舞台中央,他们既是技术的执行者,也是工业文明的叙事者,用图纸和扳手书写着新时代的价值宪章。但工程师这种身份的升维并非单向的荣耀,也被赋予了超越技术的社会责任。书中提到的“礼拜日停运争议”,暴露了技术进步与传统信仰的冲突:当铁路时刻表要求周日正常运行,清教徒的安息日传统遭遇挑战,工程师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现代性与传统性的撕裂地带。
《工程帝国:19世纪英国技术文化史》恰似一面历史魔镜,既映照着过去,也烛照着未来。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见:技术从来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文明的量尺——测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更标定着我们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文明刻度。当下我们或许更该记住19世纪英国诗人的叩问:在技术编织的时间网格里,我们是否还能听见夜莺的歌唱?这既是对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每个技术时代的终极考问。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