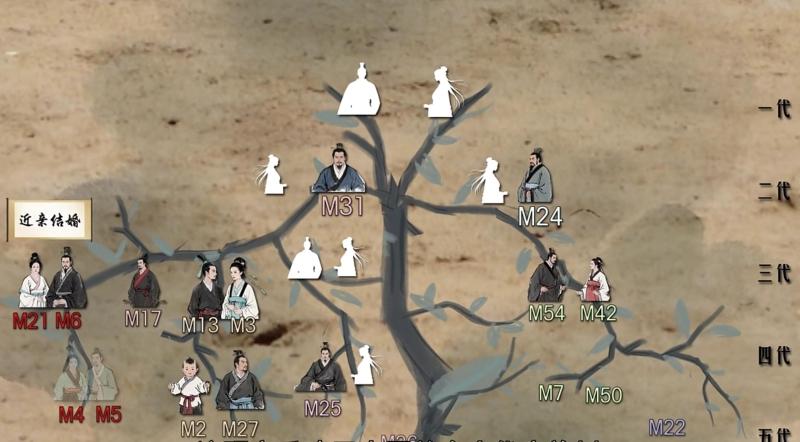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和北京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另一种栖居——走进北大学者书房”阅享会,这也拉开了2025未名书香校园阅读文化节的序幕。
活动为师生带来了一场融合学术深度与人文情怀的文化盛宴。当天是一个阴雨天。在学者对谈环节,几位老师谈起这个技术飞速变革时代阅读的价值。他们对台下的学生说,其实现在这个天气,正适合读书,读读闲书。
书籍仍然没有替代品
在碎片化阅读时代,静下心来读一本书的意义,依然重大。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戴锦华很喜欢《玫瑰的名字》这本小说。“但是第一次读到它的那种巨大的激情,现在可能很难跟同学们分享了。因为这个故事围绕一本孤本展开。”
如今万物皆可电子化,小说中描绘的用生命去保护一本纸质书的举动,可能显得有些难以理解了。“说起来非常非常惭愧,我也读越来越多的电子书。”戴锦华说,“理由非常简单,它可以调节字号。”
但电子化与否,改变的只是形式。也许实体书会遇到危机,出版业会遇到困难,但到现在为止,在今天的世界上,书籍仍然是汇集知识、传播知识和思想的唯一载体。戴锦华很清楚,大家的媒介使用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可以轻松地在网上看一段视频,听一段播客,学一段金句,但那些不是知识。“我们没看到什么新的技术能改变书籍本身的重要意义。”戴锦华强调,她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出版业、没有书店,大家无法互相推荐书籍和书单的世界。作为复杂思想的载体,书籍没有替代品。
网络空间似乎什么都有,但戴锦华仍珍视线下空间的意义。“网上‘召唤’出的是已知不是未知,是同质而不是异质。网上永远都是‘喜欢这本书的人还喜欢’‘购买这本书人还购买’。但对读书人来说,最美好的是奇遇,是未知。这是线下实体书店的价值,我们可以在其中与未知相遇。”她说。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立华也表示,文字信息密度很大,阅读和书写这种体验无法被替代。阅读状态是人主动性的高度调度,是人能够把自己的精神凝聚起来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他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等好事》的序言中写道:“阅读仍是人类精神传承最重要的途径。每个时代都会有沉静下来、超然于功利之外的阅读。我愿意相信这样的读书人的生活会永久地存续下去。”
AI越来越好,但人有人的用处
对谈中,大家不可避免会谈到AI。
北京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晔主要做文学作品翻译,他感觉人工智能对自己的冲击还没那么大。毕竟,任何可能成为文学的文本,处理起来都有一定的困难,人工智能的能力目前其实还不太够。“我感觉它的审美还有些陈旧,风格还略显油滑。”范晔评价。
其实,对范晔而言,做文学翻译是一种“需要”,而非一份纯粹结果导向性的工作。所以,就算AI能做,他也愿意自己做。
“油滑”,也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贾妍对AI生成内容的感受。她15岁的女儿能一眼识别出AI生成的图,说“AI味太浓了”。贾妍想,AI的介入,可能可以倒逼创作者创作“不难看”的东西。“逼着你更有人味一些,也许我们人文社科培养人的目标,也是让人更有人味一些。”贾妍说。
是的,AI也在对教育带来冲击,让人重新思考教育的价值和可能性。
戴锦华说,其实在进入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时代后,那种“我知,你不知,所以我告知”的教育模式就已经受到了挑战。随着AI的进一步发展,对高等学府教师的要求也就成倍提高。“老师应该成为可以提出真问题的、跟学生分享真问题的人,这更使得阅读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戴锦华表示。
杨立华则对教育中AI的使用抱有审慎的态度。他直言,有时甚至需要“限制”学生使用AI。
教育要培养人,要培养人的精神品质。“所有作业应该都‘手搓’,这样才能提升你作为人这一维度的品质。”杨立华说。他在对谈中常提到“手搓”二字。这类似一种互联网黑话,指的是某件事情完全由人工完成,没有使用高级工具,比如AI。
知识积累依然很重要。有积累,才能有判断有选择。杨立华直言,获取信息方便程度并不和人的精神品质、思考能力成正比。现在获得一本书、一段话已经如此容易,但是做学问的品质得到大幅提升了吗?
“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给你一个平均水平的东西,但如果想把自己工作做得稍微好一点,你的追求就不应该只是平均水平,就得有主动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还是要阅读,要重复训练。“任何技能,如果想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都必须经过重复训练。”杨立华说,就算以后脑机接口技术发展了,能把一个图书馆通过芯片放到脑袋里,人和人之间仍然有区别。那些怠惰的人,即使坐拥一脑袋现成的知识,都会懒得去检索,也不知道如何去检索。
前段时间,戴锦华看过“AI戴锦华”评价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她很欣慰地发现,如果她要对这部电影说点什么的话,人工智能一句都没说出来。
“它不过是昨天的我、前天的我的一个蹩脚的复制。”戴锦华感叹,“AI也许会越来越好,但要相信,人有人的用处。”
这句话赢得了全场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