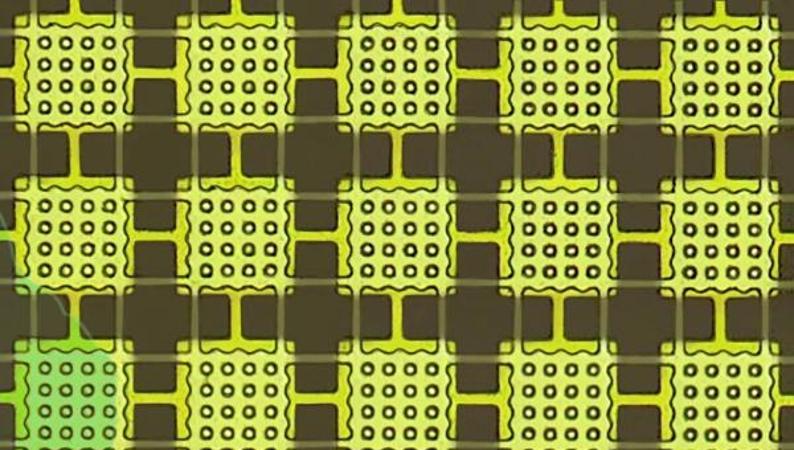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第二十届文津图书在国家图书馆发布。作为文津图书作者代表,博物画家曾孝濂上台发言。
他在台上站定,说道:“我今年,86岁。”台下观众纷纷鼓起掌来。
曾孝濂被称作“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和全国300多位植物分类学家、164位插图师一起,一共用了45年的时间,编纂出全世界最大型的、种类最丰富的巨著——《中国植物志》。几十年来,曾孝濂为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科研著作创作过2000多幅植物科学画。
“从生理上来说,我已经到了隆冬季节,但从心理上来说,我还没有画够,也没有画好,我绘画的春天还没有结束。”曾孝濂说。
写自传《自然而然》,是曾孝濂少有的画画之外的“工作”。
他原本不想写,“一个老头子,做一件事做了一辈子,有什么好写的”。曾孝濂说的“这一件事”,就是画科学植物插画。他19岁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担任绘图员;退休后,他的画笔也没有停下。
但曾孝濂发现,年轻朋友中有些人很好奇——“你们这代人,当年是怎么过的?”
那就写吧。本来想采用自己口述、其他人代为整理的方式完成,但看了别人的整理,曾孝濂觉得还不是那个意思。大家处于不同的时代,很难理解他当年的选择和心路历程。既然是这样,只好自己动笔。
为了实事求是,严谨准确,曾孝濂和老伴、老同事一起慢慢回忆,细细查找资料,完成了自传《自然而然》。
这本小书,既是对曾孝濂个人的人生记录,也是一份对中国植物科学画事业发展历程的见证。
采访中,曾孝濂好几次提到“时间”。“去年因为写这本书,花费了大半年,我太心疼了。”他心疼时间,舍不得时间,因为他还有很多画想画。
与普通植物画不同的是,植物科学画既要求精准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态特征,同时又要求与艺术融为一体,兼具科学和美。曾孝濂是大师,他的作品充满勃勃生机。那静态的花草,在曾孝濂的笔下,有着张扬热烈的生命力。
但他觉得,还不够好。
画植物科学画,一方面要准确,那是工作的准绳;另一方面要表现植物对生存的渴望,要画得准,还要画得活。
时代不同,对植物科学画的要求也不同,表现形式和手法要随之发生变化。“我们永远只能达到阶段性的成果,能画出我感觉到的60%就不错了,不可能做到极致。”曾孝濂想追求极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曾孝濂说,不必把自己当一回事,但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当一回事。他所从事的博物画,其实是个小众领域。“世人多不屑一顾,我偏觉得味道足。既要坐得冷板凳,也要登得大山头。”他曾这样写道。
现在的年轻人,没赶上编纂植物志的时代,但这是一个重视生态的时代。曾孝濂看到,有大批年轻人进入这一领域,博物画迎来了春天。
“我希望他们坚持又有定力,拿起画笔,去观察去感受去体验,练就一套自己的路子,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把我们中国的博物画向民族化、世界化的超一流水平推进。”曾孝濂期待着。
链接:
“老伴为我牺牲了自己的梦想”
在文津图书发布活动现场,曾孝濂的夫人张赞英一直都在。当曾孝濂起身准备领奖时,张赞英也站起来,一直目送老伴走到台边过道才坐下。
几十年来,张赞英替丈夫操持家里的大小事务,全方位照护着曾孝濂。
前段时间,一个节目采访了夫人张赞英。镜头里,一头白发的张赞英说,感觉自己被困住了,她一直围着曾孝濂转。“最后我就一事无成,好委屈啊。”
这段视频当时引发了很多讨论。
曾孝濂静静回忆,张赞英和自己都在一个单位工作,她做栽培育种嫁接,曾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她有她的梦想。但一家不能两个人都忙得管不了家,我们还要为孩子负责。在科研单位,你只用上班时间,是做不出成绩的,所以她牺牲了自己,成全了我。”
曾孝濂很清楚老伴的付出:“家务活,几乎都是她一个人干的。”他说,“我们走过了六十年,她有发脾气的时候,也有说狠话的时候,但是我们真正做到了相濡以沫。”
听说自己在网上很“火”,张赞英有些惊讶地笑起来:“我不知道啊。”之后,她又对记者说,“六十年的生活,其实很难用视频中的一句话概括。”
有人问,张老师您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张赞英听了,也是一笑置之:“已经风烛残年了,还谈什么梦想。”沉默了一会后,她又说:“我就努力让他多干点事吧。”
文津图书发布活动结束后,大家让曾孝濂和夫人合张影。
曾孝濂大方地搂过了张赞英的肩膀,两人一起对着镜头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