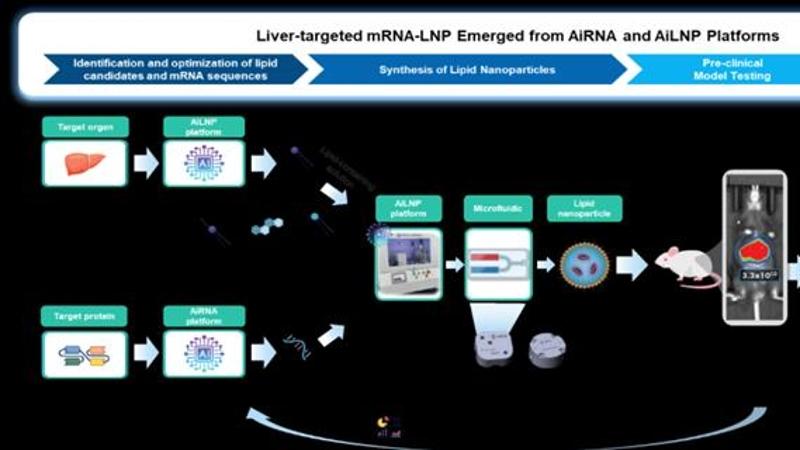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吴叶凡 通讯员 杨为玥
一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经过加工后能够用于炼钢、发电、造车……“点石成金”的关键一步,就是矿石加工。对矿石进行加工在我国已经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浮选则是矿石加工的重要环节,决定着矿物的最终品质。
从亦步亦趋的“跟跑”到不断创新的“领跑”,我国浮选装备研制已走过50余年的岁月。在浮选装备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过程中,我国浮选装备研究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矿冶集团”)首席科学家沈政昌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下,浮选装备也迎来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近日,沈政昌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要加快检测仪表的研发工作,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浮选装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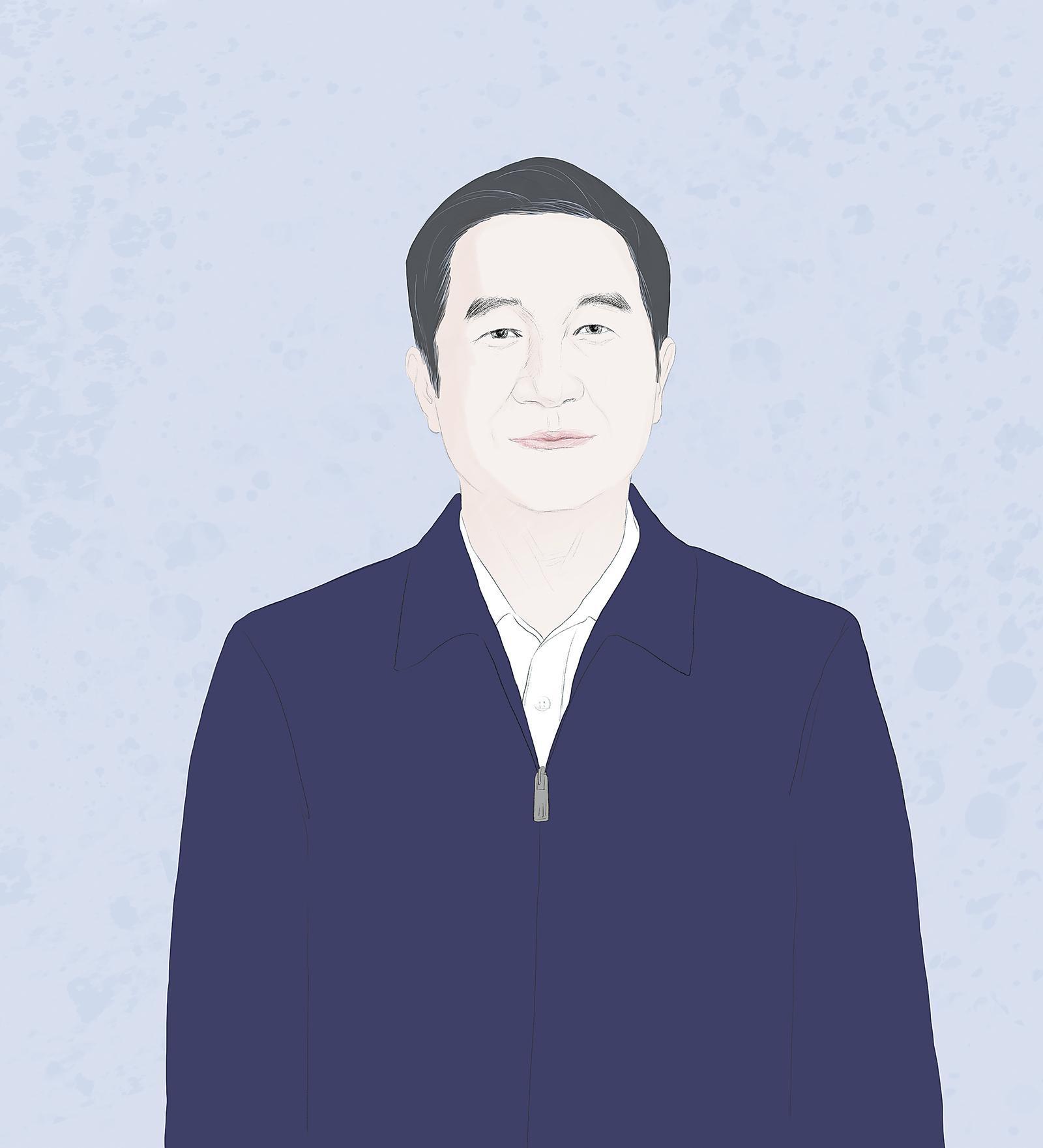
走出自己的浮选装备研制道路
记者:请您介绍下什么是浮选技术?
沈政昌:浮选是一种根据矿物颗粒表面物理化学性质的不同,从矿石中分离有用矿物的选矿方法。在我国古代,浮选法就已经被用于金银淘洗加工过程。古人利用金粉的天然疏水性及亲油性,用沾油的鹅毛刮取浮在水面的金粉,使其与尘土等亲水性的杂质分离。
19世纪末,浮选作为一种选矿方法被明确提出。1904年,浮选设备在澳大利亚首次获得工业应用。100多年来,浮选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步实现了浮选机多样化、系列化、大型化和自动化。目前,世界上约有90%的有色金属和50%的黑色金属矿石采用浮选法处理。除了冶金,浮选还广泛应用于造纸、农业、食品等行业。
记者:您是如何与浮选装备领域结缘的?
沈政昌:我上学时对物理、化学两个学科很感兴趣。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发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有“物理化学”专业。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我当时对专业也不太了解,只觉得“物理化学专业”能够既学物理,也学化学,就报了这个。
但录取结果一出,我发现自己被调剂到了同校的矿山基建工程设计专业。虽然没去到自己的第一志愿,但我学习后发现,矿山机械领域和物理力学关联性很强,我对此也很感兴趣,就一直在这个领域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矿冶集团,进入浮选设备研究组,从此就与浮选装备结缘,一直到今天。
记者:上个世纪,我国浮选装备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
沈政昌:我国在浮选设备研究方面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才开始仿制苏联的米哈诺布尔型浮选机。20世纪70年代,我们开始自主研发浮选设备,陆续研制了4立方米、8立方米、14立方米容积的设备。当时我们主要跟随国外研究的脚步,处在“跟跑”阶段。
那时的科研条件比较艰苦,实验室的各种测量手段都比较匮乏。我至今还记得,40多年前,刚工作的我跟着几位老同志在湖北大冶做20立方米浮选机试验。大概是三月底的一天,天气还很冷,为了测量浮选机内的流场情况,几位老同志轮流脱下衣服,直接跳进浮选机内,用身体感受流体状态。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老一辈矿冶人的精神,这件事令我至今难以忘怀。
打破“跟跑”这一局面是在21世纪初。2001年,我国第一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50立方米大型浮选机试验成功。在选矿理论和机械结构等方面,这台浮选机都走出了一条和国外浮选机不同的道路,不再是“亦步亦趋”。因此可以说,这台浮选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大型化浮选装备与国际同行站在了同一梯队。
实现从“有”到“强”的跨越
记者:初步实现“并跑”后,我国浮选装备如何一步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沈政昌:2010年前后,我国浮选装备完全实现了与国外设备的“并驾齐驱”。当年,我国200立方米和320立方米浮选机先后研制成功,打破了特大型浮选设备一直被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320立方米浮选机也是当时世界上容积最大的浮选机。此外,我国在粗颗粒浮选机、细颗粒浮选机细分领域的设备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多进展。
如今,我国已经在很多领域实现“领跑”。比如在国际上,我国是最早研制成功680立方米和800立方米浮选设备的国家。现在国外还没有800立方米浮选机。我们还成功研制了利用流态化原理进行浮选的新型设备。通过它,我们可以提前把无用的脉石矿物剔除掉,降低后续处理过程的能耗,从源头减量,推动矿产资源的绿色低碳开发。它也可以对尾矿进行再回收,实现宝贵矿产资源的极致利用。
记者:我国已经取得这些成就,为何还要不断技术创新?
沈政昌: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矿产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小汽车到手机,都离不开矿产这一重要原材料。另一方面,现在矿产资源面临逐渐贫杂化的问题,资源禀赋较好的矿山基本枯竭。以磷矿为例,以前许多磷矿能达到30以上的品位,采出来基本上就可以直接用于生产磷肥,但如今大部分磷矿的品位连25、26都达不到。现在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很快,磷是制作电池的重要原料。资源越来越短缺,需求却逐渐变大,面对这一矛盾,我们必须从工艺、装备、药剂、智能化等方面着手,不断升级浮选装备,提高生产效率。
记者:把浮选机容积做大难在哪里?
沈政昌:从几立方米到现在的几百立方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大或是把构件尺寸做大的过程。以泡沫浮选过程为例,这是矿物与杂质或一种矿物与另一种矿物分离的方法。无论多大的容积,我们都要保证浮选机内部流体动力学状态相似,否则就不能形成有效矿化,目的矿物就沾不到矿化泡沫上。另外,当矿物附着到泡沫上之后,我们还得让泡沫及时脱离矿浆。当浮选机容积变化,这些关键难点都要重新研究试验。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不断把浮选机做大,是因为矿山实际生产提出了这一研制需要,并非盲目求大。评价一台浮选机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合适”。一台浮选机要切合所处矿山规模、矿石种类,实现经济效益、绿色低碳、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平衡。
记者:如今,我国浮选机已出口南非、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有没有遇到困难?
沈政昌:在早期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国人在设备研发等方面都不行。我记得有一次,澳大利亚的一个矿山本来决定引进我们矿冶集团的两套装备,但矿山后来更换的新经理认为两套装备都用中国的设备风险太大,因此最后只用了一套。但投用后,他们发现,我们的设备无论在功耗、运转可靠性等方面,都优于国外设备,而且价格不到国外的一半。
这次走出去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些经验教训。比如浮选机里的电机,对方要求有澳大利亚的认证。当时我们这台设备的大电机是有认证的,就放心地签合同了。没想到用了快一年的时间后,对方突然找到我们,说机器里面的几个小电机没有认证,要求更换。虽然小电机的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是得按照合同支付违约金。吃一堑长一智,这件事告诉我们,设备“走出去”,不仅要靠过硬的性能,也要摸清当地的标准执行情况,符合当地标准体系。
记者:万事开头难,今天矿冶集团的浮选机已经赢得了国际的认可。
沈政昌:是的,我觉得这得益于改革开放后,我国很多大企业在国外投资矿山,他们在当地使用国产设备,起到了示范作用。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向国外展示的机会。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擦亮中国浮选机这张名片,尤其要确保重要元器件、系统软件的自主可控。
以科技创新促传统产业升级
记者: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您认为浮选装备转型升级的方向是什么?
沈政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突出特征是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浮选领域也不例外,提升装备的数智化水平是我们未来科研的着力点之一。此前,我们提出了高性能大型浮选机发展路径必须实现设备状态参数控制、工艺过程参数控制、浮选动力学过程参数检测和控制、信息化和运维智能化等五个方面的整体发展。
同时,近年来国家加快矿业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推进绿色矿山建设。作为矿山生产的重要一环,我们也要努力推动浮选装备向高效化、绿色化、低碳化发展。高效化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即通过科技创新,把原本技术条件下难以选出的有用矿物“选出来”。
绿色化、低碳化的目标则是减少资源消耗。就能耗来说,以前选一吨铜,可能需要两三度电,现在只需要不到一度电。别看这节约的一两度电不起眼,现在一个大型矿山平均每天要处理几万吨的矿石,因此在选一吨铜时能够节约一度电,整体带来的就是很大的收益。通过浮选装备创新,我们不仅可以节约电能,还可以减少起泡剂、调整剂等药剂的使用量,达到综合的降碳节约。
记者:转型升级是否带来了新挑战?
沈政昌:挑战和机遇一定是并行的。在数智化转型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很多需要突破的难关。从外部看,现在地理位置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矿山,基本都面临资源枯竭的现状,目前主要开展矿山土地复垦或是回填;大部分具备开采条件的矿山,都位于较为偏远的山区,甚至是海拔四五千米的地带,生产条件艰苦,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数字化转型。
从技术本身看,选矿过程离不开对矿石、矿浆相关参数的检测。但目前,包括各种传感器在内的检测仪表,还远远不能适应矿山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需求,离智能化就更远了。举例来说,现在行业检测矿浆浓度、粒度、pH值等参数的方法还比较“粗糙”,有的工序要靠工人上手去摸、用眼去看,还处在凭经验、凭感觉的阶段。一些创新方法在实验室里表现不错,但难以应用到现实的工业生产中。在实际生产中,这些方法给出的数据不太准,可靠性比较差。因此,选矿过程还是离不开人工操作,距离实现无人化、少人化、数字化生产,还面临层层挑战。
记者:为了推动浮选装备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您认为应如何破解这些难题?
沈政昌:推动数智化转型,是一个急不得也慢不得的过程。我认为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扎实地逐步推进。
第一,无论是数字化还是智能化,数据都是最基础的要素。要把数据“拿出来”,检测设备是关键。所以,我们要加快研发一批能够精准感知整个浮选过程的元器件。近年来,我们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比如,研制了自动充气量测量仪,矿浆相水下相机,气泡负载率测量仪和气泡特征参数测试仪等自研仪表和装置,实现了浮选过程复杂多相流环境下的测量和在线数据获取。
第二,开发行业大模型。目前,矿冶集团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十个场景,开发了十个大模型,其中一个就是浮选装备的大模型。它可以用于解答各类专业技术问题,还可以把它用于浮选装备的控制,提高操控的精准度。
现在浮选装备大模型用的算法和通用大模型基本相同。如果要让行业大模型更了解行业,关键点还是数据。相比于其他领域,浮选装备大模型数据相对完备,但很多底层数据仍是缺失的。所以,研发检测仪器和开发行业大模型,这两步要相辅相成,协同推进。
记者:您认为实现浮选装备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注重哪些方面的问题?
沈政昌:除了数字化、智能化、高效化、绿色化,我认为还要注重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比如黄金开采。现在很多金矿都位于地下,矿井深度能达到几千米。按照惯例,人们通常把地下开采的所有矿石都运输到地面上,再进行加工,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消耗,因为矿石中黄金含量不高,运上来的大部分石头都没用。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浮选装备直接置于地下,进行初级加工,哪怕减少一半的矿石运输量,都能节约很多资源。
所以,浮选装备技术的创新,要和矿山各个生产环节、链条相结合、相匹配,实现体系化的创新协同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致青年科技人才】
青年人想要成才需要“盯住一件事”。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放弃,要找到自己的长处。只有找到自己的长处,才能坚持下去,做成一些事。
此外,现在的社会,靠一个人单打独斗是很难出成绩的,一个团队、一帮人、一个平台,可能比一个人的才华更重要,所以青年人要学会合作,重视团队的力量。
——沈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