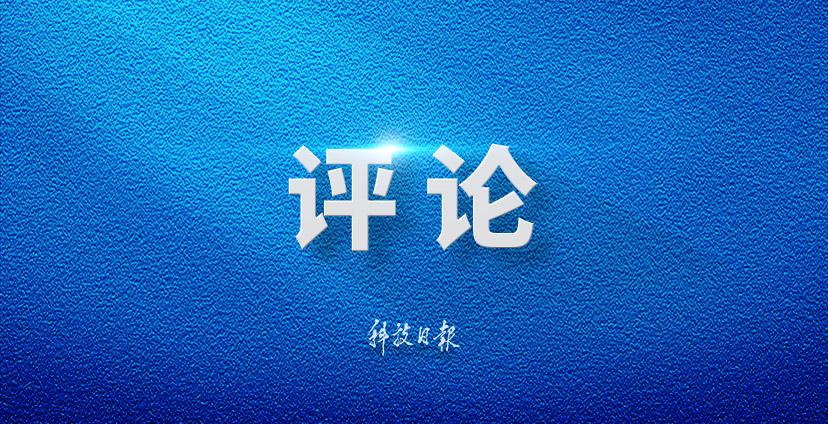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吴叶凡
有人说,如果没有他,人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解北京;有人说,如果不是他,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他就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
侯仁之生于1911年。那一年,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相继爆发,中华大地风起云涌。成长在风云跌宕的年代,侯仁之经历了国家一次次的内忧外患,目睹了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家国情怀从小根植于他的心中。
“出生之时,辛亥风云正炽;幼岁体弱,几不得进学……”在作品《晚晴集》自序中,侯仁之记录了他辗转求学的经历。从德州到济南,再到通州……波折的求学路上,侯仁之常思考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学习对饱经磨难的国家有什么用。
顾炎武有言:“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这句话带给侯仁之内心巨大的震动:“我在图书馆读他的书,泪就掉下来。我想,做学问也可以为祖国建设服务。”1932年,凭借自身的勤奋刻苦,侯仁之考入燕京大学。
1940年,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在燕京大学任教。校务长司徒雷登向他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希望他在教学之余,兼任学生生活辅导科科长,负责处理新生从入学到毕业离校期间所有的生活难题。
侯仁之一开始稍有犹豫,他想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教书治学当中。但他的导师、史学家洪业的一席话打动了他。洪业郑重地叮嘱他: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能够帮助同学成长。
洪业的话不无道理,自1937年北平陷落后,许多大学纷纷搬离。留在北平的燕京大学如同一座教育孤岛,日本侵略者早已把它视作“眼中钉”。
1940年6月,燕京大学成立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侯仁之担任副主席。在与学生们的交流中,侯仁之发现,一些学生愿意参加抗战,还有的要参加八路军。
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这是何其冒险的一件事。但面对这些一腔热血的学生,侯仁之的胸膛也仿佛烧起一把火。为了事情万无一失,他和多位同事一起,商量出最周密的计划。
1940年冬天,侯仁之亲自将10多个学生分批送上了开滦煤矿的运煤船,学生们计划走水路抵达上海,再进入内地。为了保险,学生们还装扮成商人模样。最终,十几人安全抵达上海后,如同星星之火一般,“播撒”到中华大地。
这之后,经侯仁之联系,从燕京大学转送到根据地的学生共有3批十几个人,有的经西安最终到达延安,有的直接奔赴抗日前线。
然而,秘密的行动还是让日寇有所觉察。平静生活中出现的种种不寻常,无不提醒侯仁之,他可能已经被盯上。1941年冬,侯仁之为了陪伴临产的夫人,前往天津。临走前,他留下天津的地址,为的就是告诉日寇,并非有心躲藏,要想捕人,就在明处。
不幸的是,不久后,侯仁之在天津被捕。入狱后他才了解到,从1941年底到1942年,日本宪兵队以“抗日嫌疑”的“罪名”,先后逮捕了燕京大学多名教职工。
侯仁之曾对人讲起这段经历:“日军在军事法庭上判决我,‘罪名’现在想起来真可笑,我的‘罪名’是以心传心、抗日反日。他们审问我好几次,我就不说。”
在狱中,侯仁之受到不少欺辱。侯仁之的儿子曾回忆:“父亲过堂时,鬼子上来先打了个大巴掌,眼镜都被打得不知去向。”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侯仁之却泰然处之,在狱中构思出《北京都市地理》腹稿,这份腹稿也成了侯仁之经典之作《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起点。
一本危难之作,彰显侯仁之的气节。“父亲以此明志:本业之不可废,志气之不可夺。”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说。
如今,斯人已去。但侯仁之先生的不屈气节和抗争精神,将被一代又一代人铭记。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