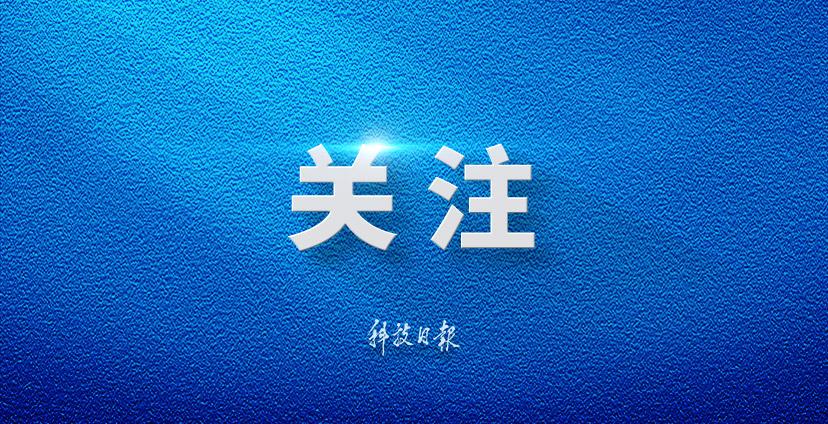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代小佩
编者按
80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科学家走出象牙塔,以科技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在前线,他们研究枪炮弹药、军事通信、战地给养;在后方,他们研究农业生产、民生工业、基础科学……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筑起一道道科技防线,为抗战胜利作出特殊贡献,也为硝烟中的学脉传承留下火种。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本报推出特刊,重温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们科学救国的故事,赓续他们科学报国的精神。
8月29日,“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拉开帷幕。穿行于一件件展品之间,思绪又被拉回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挑起的战火下,神州陆沉,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一群手握试管、图纸、标本的中国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共赴国难。
彼时的中国,现代科学起步不久,基础薄弱、设备匮乏。不过,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科学家群体就已自发组织动员,以赤子之心,在抗战烽火中筑起特殊防线。
他们,或以精密仪器守护信息阵地,或以田间试验筑牢粮仓根基,或以教育薪火延续文明血脉,在烽火中书写“科学救国”的壮阔史诗。
闯技术难关,坚持自力更生
“今日世界利弹怪艇咄咄逼人,舍科学无以立国。”
物理学家严济慈这句话,道出了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的共同信念。面对国外技术封锁与军事威胁的双重绞杀,他们用智慧劈开了一条自力更生之路。
昆明黑龙潭,一间破庙,严济慈带领团队成员手工打磨镜片的“沙沙”声,与前线的枪炮声遥相呼应。
严济慈从居里夫人实验室获得珍贵的石英晶体样本,并基于空心水晶圆柱体相关理论研发出抗战利器——全新无线电发报机稳频器。
这项成果极大改善了我国战时电信技术,满足了驻昆明美军和驻印度英国皇家空军的应急器件需求。
四川乐山,化学家侯德榜经历了500多次试验。
在当地,索尔维制碱法因盐料成本高昂面临困境。侯德榜另辟蹊径,发明了侯氏制碱法。该方法不仅使所需设备减少1/3、成本降低40%,而且将盐的利用率提高至96%,同时能把生产废物转化为化肥。
这项突破为抗战时期工业发展及大后方的民生保障作出巨大贡献,更为世界制碱技术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钱塘江畔,桥梁专家茅以升的故事却显悲壮。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驶过了第一列火车。然而,喜悦之情还未平复,茅以升就接到了炸桥的命令。为了不让大桥落入日军手中,这座由茅以升历时两年半建成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通车不久便被炸毁。
“抗战必胜,此桥必复!”茅以升的誓言背后,是科学家视民族大义为根本的崇高追求。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带着精心保存的14箱资料回到杭州,克服重重困难,成功修复钱塘江大桥。
在延安土窑洞,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的创新显示了“土法上马”的智慧。
仅有一台手摇车床、几把老虎钳……罗沛霖以猪油代替润滑油,用木头制作绝缘零件,研究通信材料。这位无线电专家,在黄土地成功造出60多部电台并将其送往抗日前线,让八路军通信装备脱胎换骨。时任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曾笑言:“有了罗工程师,我们就不是‘土八路’了。”
抗战时期的中国科技史,写满了科学家在艰难中开拓与坚守的故事。
科学家把碳化后的核桃壳做成活性炭,用来研制防毒面具并支援华北前线……“前线的迫切需求,让科学家们将书本知识与战场实际紧密结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公说。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晓告诉记者:“当时,科学家们清楚看到中日科技实力差距,但他们仍然坚信中国必胜,共赴国难,体现了中国科学家面对民族危机的担当。”
守烽火学脉,呵护科学火种
途经六省,历时两年半,行程2600公里……这是一条“文军长征”路。
1936年4月,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面对学校师资匮乏、基础设施差的局面,他大量引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坚持招收一流学生,让校风焕然一新。
然而,一年后,杭州沦陷,浙江大学被迫西迁。
西迁路上,竺可桢带领师生“驮”着图书仪器,一边跋涉,一边上课。敌机轰炸时,他们钻进防空洞继续讨论课题;没有地方上课,师生们就把庙宇祠堂当教室,结茅架竹建校舍。
校舍简陋、物资匮乏,科学家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取得一系列成就。
数学家苏步青在遵义湄潭靠种地养活家人,写出了《射影曲面概论》,他也被学生称为“菜农教授”。物理学家王淦昌一边放羊一边研读论文,发表重要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这位“羊倌教授”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在这场大迁徙中,浙江大学学院从3个扩展到7个,还培养出26位院士,成为烽火中的学术灯塔。
同样守护科学火种的,还有物理学家钱临照。
1937年冬,日军包围北平,钱临照与同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白天整理文献作掩护,深夜从后门将显微镜、光谱仪等精密仪器伪装成普通货物,经塘沽港转运。
历经半年辗转,这批设备抵达昆明。钱临照发明了“自准直法”,用普通显微镜改造出毫米级曲率半径球径仪。该方法不仅破解了光学仪器生产瓶颈,设计原理更被全国厂家沿用至改革开放初期。
化学家陈康白播撒的科学种子,长在黄土高坡。
拒绝诺贝尔奖得主阿道夫·温道斯的挽留,陈康白带着成包书籍、器材奔赴祖国。在延安,他受命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纸不够用,在陈康白带领下,化学家华寿俊等人用马兰草造纸。难民纺织厂生产上遇到瓶颈,陈康白和工人一起吃住,共同建厂房、调设备。
这所诞生在窑洞里的学院,培养出近500名“革命通人、业务专家”,后来演变为北京理工大学,成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人才的摇篮。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坚守,更是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制作糕点出售,化学家曾昭抡办肥皂厂生产肥皂,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用云南虫蜡制蜡烛……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者们以乐观对抗困境。
王公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科技领军者。
从杭州到遵义,从海外到黄土高坡,从北平到昆明,中国科学家们用坚韧的意志证明:仪器可以被摧毁,校舍可以被炸毁,但中华民族的科学精神永不磨灭、教育火种永不熄灭。
护万家安宁,筑牢民生根基
“大虫不杀,杀小虫何用!”1938年,意大利那波利大学的昆虫学博士周尧放弃优渥条件,回国穿上军装,奔赴河南兰考前线。
结束戎马生涯后,周尧投身西北农学院,开创“以虫治虫”生物防治法。他用寄生蜂制服小麦吸浆虫,拯救了黄河流域千万亩麦田。他在古籍中发掘中国古代昆虫学成就,写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初稿)》,在世界昆虫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川荣昌的田埂上,小麦育种科学家沈骊英的故事令人动容。
这位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的女科学家,带着种子箱和年幼的孩子辗转数千里,在中国土地上播撒小麦种子。沈骊英双腿罹患疾病,时常剧痛难忍,可她始终放不下田里的试验,便请人将自己抬到田间,坚持观察记录。沈骊英从1700多个小麦品种中筛选出9个,年均推广种植超过300万亩。
不过,这位被陶行知称为“麦子女圣”的科学家,却在44岁时倒在实验室,猝然离世。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基础薄弱,许多生活必需品都无法生产。原本在山西太原理化研究所负责研究防毒面具的化学家钱志道来到延安,带领团队用厕所墙土熬硝、设计制造酒精蒸馏塔、编写课本开办夜校,一年建起紫芳沟化学厂。该厂既产子弹、手榴弹,也产火柴、酱油,让封锁中的边区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这样的事迹不胜枚举。农学家乐天宇提出开发南泥湾的建议,让贫瘠的黄土高原长出粮食。石油专家陈振夏接手破败的延长石油厂,从零开始重建。延长石油厂生产的石油满足了边区工业、农业与军事需求。
医疗卫生领域的守护战同样激烈。
这是一组令人揪心的数据:抗战相持阶段,非战斗减员与战斗减员比例高达5∶1,因疾病、营养不良死亡的士兵远超战场牺牲者;后方民众年死亡率达3%,每年由于医疗卫生问题死亡的民众达675万人。
面对危机,科学家们挺身而出。医学病毒学家汤飞凡在大后方开展疫苗、血清研究,研发的伤寒疫苗等在战时发挥重要作用。营养学家沈同奔赴长沙会战前线,调查1万多名士兵的营养状况,为改善军粮制度提供科学依据。农学家罗登义发现贵州野果刺梨维生素C含量极高,便推广用刺梨替代维生素药品,解决民众营养匮乏问题。
科学家们秉持科学精神,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人民。他们深知,持久战的底气不仅在前线的枪炮,也在后方的仓廪充实与民生安定。
承先辈风骨,不负担当使命
严济慈的石英片、侯德榜的制碱法、茅以升的桥梁图纸、周尧的昆虫标本……这些带着硝烟味的科学遗产,早已化作精神的基因深深融入民族血脉。
“在和平年代,回望抗战岁月,整理研究中国科学和科学家的遗产十分重要。”王公说。
战时的科技探索,为战后科技发展埋下伏笔。
汤飞凡的青霉素研究、微生物学家童村等科学家的后续攻关,让中国逐步掌握抗生素生产技术。清华航空研究所对西南木材的调研、关于风洞建设的经验,为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侯氏制碱法、延长石油厂的重建,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的重要起点。钱临照的“自准直法”、真菌学家戴芳澜的真菌调查数据,至今仍在相关领域发挥作用。
人才培养的成果,影响深远。
抗战期间成长起来的科技工作者,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脊梁”:诸多“两弹一星”元勋在战时完成学业或开始科研事业;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工作者,成为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专家,推动医疗工作的建制化……抗战时期培养的科技人才,撑起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半壁江山”。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科学精神。
“抗战前,中国科学家多延续国外研究课题,用外文发表成果。抗战中,他们直面中国需求,将国外知识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实现了‘科学中国化’。”王公说,“这不仅解决了战时难题,更确立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科研导向,让科学真正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刘晓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科学家的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源泉,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精神,都能在那段烽火岁月找到源头。
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要节点,穿越历史烟云回望,我们不难看到:这群科学家在破庙里、土窑中、田埂上的坚守,展现了技术突破的智慧、积极乐观的态度、“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赤诚,为后世铸就了精神丰碑。
这是科学救国的信念。从严济慈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国研制稳频器,到周尧脱下西装穿上军装,再到竺可桢喊出救中国只能靠自己……他们始终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这是乐观坚韧的意志。苏步青种地不辍科研,王淦昌放羊不忘思考,梅贻琦命名“定胜糕”传递信心……他们在物资匮乏、生命受威胁的环境中,以积极心态挺过艰难岁月;
这是不断创新的智慧。用由核桃壳制成的活性炭做防毒面具,用水缸制作反应塔,用蓖麻籽油替代润滑油修飞机……无数例证说明,真正的创新是“条件不足时的逆流而上”。
“战时科学家在困境中坚守的精神,为我们今天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大力量。”刘晓说。
穿越历史风云,抗日战争中锤炼的科学家精神依然给后人以启迪:科学家的前途命运,永远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科学家的担当,将在民族复兴征程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