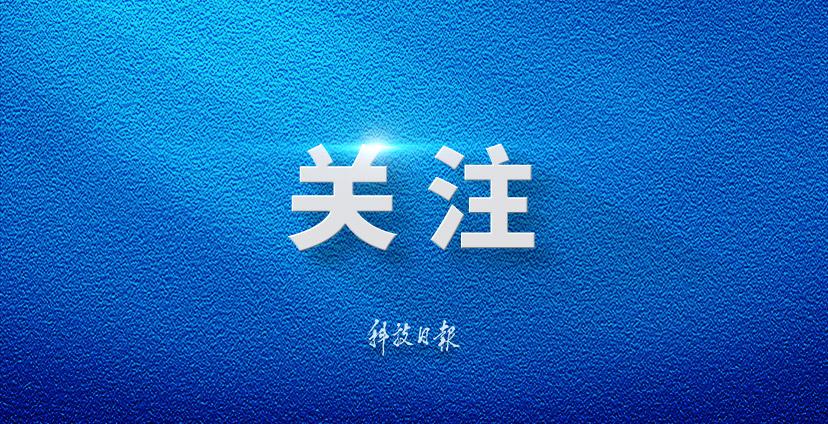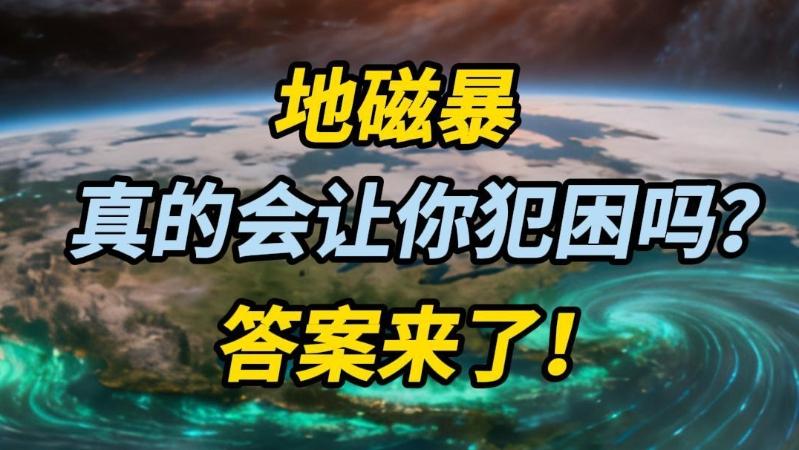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孙明源
“康熙皇帝的生父其实是洪承畴!这样历史上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近日,关于“洪康熙”的假说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历史板块传得沸沸扬扬。
网友的热议得到了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11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副教授严实在网上发文称,“洪康熙”假说缺乏证据,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从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
严实是首位通过DNA研究确定努尔哈赤Y染色体类型的学者。不过,一些支持“洪康熙”的网友仍在对严实的结论提出疑问,这些天来,严实也在通过不同渠道持续作出回应。
这些疑问的共性是什么?严实坚持“洪康熙假说不可信”的核心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在这一问题上发声?科技日报记者与严实取得联系,请他深入剖析“洪康熙”争议的来龙去脉。
“这是个科学方法论问题”
记者:你提出“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依据的研究结果是怎样的?
严实:2019年时,我曾采集到一位现代爱新觉罗家族后人提供的样本,有可靠的谱系学和其他证据表明,他是雍正第五子弘昼的后代。
测试结果表明,他的Y染色体DNA单倍群是C2b1a2b1-F14751这支,与努尔哈赤相符。基于这一证据,以及奥卡姆剃刀法则,我们有理由接受“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的父系传承没有问题”的结论。
记者:你说的奥卡姆剃刀法则,很多人并不了解,请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严实:奥卡姆的威廉是一位古代哲学家,奥卡姆剃刀法则是由他提出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作出科学推论时,应基于现有证据选择假设最少、逻辑最简单的理论。
所有缺乏证据的假设,或者无法被证实存在的影响因素,都应该被“剃”掉,除非它们得到了新证据的支持。
记者:网上有人质疑你的研究说,弘昼可能不是雍正皇帝亲生的,或者弘昼的后人也曾被“换种”,这些都是你说的缺乏证据的假设?
严实:是的,这些缺乏证据的猜想在科学理论中就应当被搁置。事实上,这些假说绝大多数也是严重违背历史常识的。
比如有人说“弘昼是雍正皇帝抱养的,雍正想掩盖自己不能生育的秘密”。可是雍正的子嗣虽然不如康熙和乾隆那样多,实际上也有好几个,难道都是抱养来的?
另外,皇帝没有子嗣在清朝也不是什么需要处心积虑隐瞒的秘密。清末光绪帝没有子嗣,宣统帝出自别支,被定为光绪宗法上的儿子,这事人尽皆知,也没有人去隐瞒。
就算雍正真的抱养过孩子,而且真的有意隐瞒,要知道清代中期档案文书已经高度发达,皇帝抱养宗亲孩子这样的大事,怎能做到不留书面痕迹呢?
大多数阴谋论式的猜想都有类似的问题。如果我们不采用奥卡姆剃刀法则,不接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科学方法论,此类添油加醋的假说无穷无尽,就无法形成任何有效结论了。
记者:一些网络言论表示,“洪康熙”假说之所以有说服力,是因为它能够解释历史上的很多现象。例如称康熙帝13岁生子是因为改过年龄,洪承畴对清朝非常卖力是因为皇帝是他儿子等。你怎么看?
严实:“说得通”跟“有科学依据”是两码事,“说得通”不代表真实。
例如,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类无法理解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神灵在发挥作用,是不是全都说通了?
但是,科学不能接受“神灵”这样一个概念,因为它的存在没有证据支持。“说得通”的理论可能有无数种,但是要判别哪种理论可靠,就得拿出证据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科学伦理是重要准则”
记者:说到证据,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你为什么不去寻找更多更直接的证据?比如康熙不同儿子的多位后代,或者干脆拿出康熙本人的检测结果,那不是比弘昼更有说服力吗?
严实:首先,弘昼是康熙的孙子,从其后人身上得到的证据,效力已经很充分了,原因我在上面已经阐明。
另一个关键点在于,很多网友把科研想得太简单了,和其他科学领域一样,分子人类学开展研究的第一准则,是科学伦理。无论是采集古人DNA,还是现代人DNA,都有需要重视的科学伦理。我们发表论文,也需要经过学校和期刊伦理委员会的审查。
记者:请讲讲科学伦理对你开展研究的影响。
严实:先说采集现代人DNA样本的情况吧。
网上有人问,为什么不去找几百个爱新觉罗后人做测试,找康熙其他后人做测试?其实,现实当中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测试的都不容易。
我们必须向受试者提供知情同意书,完整说明我们关于样本采集、保存、流转、销毁的全部情况,以及我们的研究目的,获取哪些信息,这些信息将以何种程度在哪些渠道披露。
经历层层背景筛选和寻访后,我们即使找到了合适的人,对方也很可能不同意参与研究,我们必须尊重对方的决定。
现实中人的权利和意愿,优先级永远高于我们的研究需要,也高于网友对个别历史问题的好奇心。
还有些网友误会了学者的“官方”背景,以为学者可以像公安部门一样采集公民遗传信息。我国是法治社会,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都要严格遵守法律。公安部门依法收集的公民信息与科学研究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科研中采集的样本和信息也不会泄露到无关机构。
再说古人DNA采集的情况。古人的遗体,包括头发、干尸等,很多归文物保护部门管理。分子人类学家要采集样本,需要相关部门的合作,但是征求同意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拿我知道的一件事举个例子:之前有研究团队从某帝王陵墓取得遗体样本,不过由于样本保存条件太差,研究没能得到什么结果。后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阴谋论,说是研究结果被刻意隐瞒了,这件事对陵墓的管理方来说是徒增烦恼。
所以,从古人陵墓当中获取样本也不容易。文物保护部门同样有需要遵守的法规,考古学家也有他们的职业伦理。法律和伦理的分量,始终是高于公众的好奇心的。
“我的立场是科学本身”
记者:在科研伦理等各种因素制约下,我们暂时得不到更“直接”的证据了。这样看来,个别坚持相信“洪康熙”的人可能不会改变观点。
严实:有人脱离了科学方法论,单纯从立场和价值判断出发认识世界,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不管多少证据现身,阴谋论者都可能坚持己见。
如果我们非要证明康熙是顺治的儿子,那么理论上我们必须得到两个人本人的DNA样本,比对Y染色体还不够,还得比对常染色体。因为Y染色体类型一致也不能确定父子关系,也有可能是叔侄。
事实上,如果有人坚持“洪康熙”说法,或者认为弘昼不是康熙的亲孙子,应该请他提供证据。
谱牒也好,康熙其他后人的检测结果也罢,请拿这些证据说话,但是目前我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记者:作为一名学者,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件事上发声?
严实:因为这些讨论涉及我的专业领域分子人类学,恰好又与我做过的研究有关,作为一个学者,我有责任跟公众科普相关知识。
我看到网上有人讨论我的“立场”,实际上我的立场只有科学本身,我坚持事实和证据不应妥协于价值判断。
多年来,我做过很多分子人类学相关科普,讨论过的问题也不只有“洪康熙”这一个。看我之前的发言就知道,我没有先入为主的立场。
记者:总的来说,你认为这次关于“洪康熙”的网络讨论给了我们哪些启示?
严实:我认为公众应该加强对科学方法论的认识,相关内容或许可以成为中学教育内容的一部分。
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依据事实和逻辑而非价值判断看待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提升的素养。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