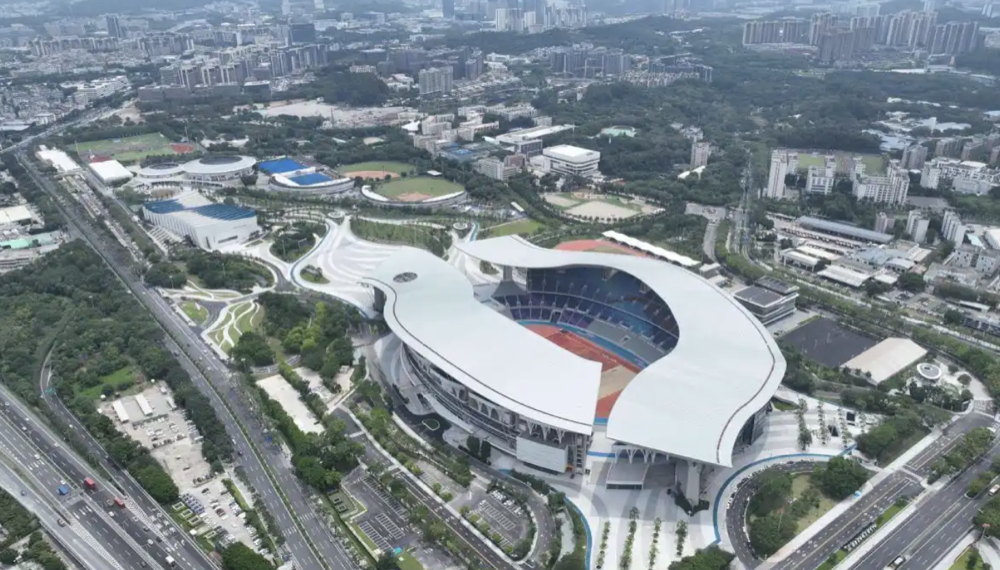梁永刚
豫中乡间,蒺藜是一种平卧蔓生的寻常野草,田畴阡陌,房前屋后,随处可见它的身影。翠绿的藤蔓,发达的根系,哪怕是在最贫瘠的荒野,它也能以低过所有野草的卑微姿态,匍匐成一地葳蕤。
蒺藜萌生于春日,从地下冒出瘦弱的幼芽,柔嫩嫩,纤细细,顶着几片淡绿的羽状叶片,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用不了多久,蒺藜长长的藤蔓,开始向四周铺展,宛如一条条游走的青蛇,所经之处蔓叶缠绕,绿意葱茏。在乡间诸多野草中,蒺藜是极其谦恭的,从青涩到衰老,始终躬着卑微的身躯,贴着土黄的地面。
初夏时节,麦子黄了梢,蒺藜也开出了花,羽状的扁圆绿叶,簇拥着一朵清新玲珑的小黄花,带着一种素雅,透出一种温润,让人无法相信眼前的可人小花,凋零之后会长出布满尖刺、令人生畏的球状果实。行走在乡间的阡陌田垄,很少有人会在意小小的蒺藜花,奉行实用主义的农人,更多在意的是植物的果实。
夏末之时,花谢以后,蒺藜开始结果,一开始果是绿色的,很嫩,刺也很软,一捏一股水,脚一踩就烂。放牛割草的农家娃赤脚走在草地上,丝毫不用担心藏匿在草中的蒺藜果实,即便是偶尔有一些早熟的果实,长出了些许棱角,但踩在长满厚茧的脚下,人也没有什么感觉。此时,牛羊对掺杂在青草中的蒺藜果实,也不是特别反感,毕竟软刺对嘴构不成威胁,往往是连同青草一并咽下了肚。
秋收过后,蒺藜果实的青绿果壳开始变黄变干,刺硬且尖,异常锋利,不小心触碰到它,能刺破皮肤扎到肉里。这个时候,牛羊似乎也觉察到了草丛里暗藏的“杀机”,吃草时也格外小心,看见蒺藜的身影就绕开了。乡谚说:“蒺藜拌草,不是好料。”成熟的蒺藜有刺,即便是无意中掺杂到了草料中,牲口也不吃。割草的人留意着蒺藜,看到眼前有片好草,但中间长着两棵蒺藜,就先用镰刀割断蒺藜根部,提溜起长长的藤蔓,扔到一边,再接着割草。
在童年和少年的漫长时光里,我对蒺藜抱有很大成见,或者说怀恨在心,一听到有人说蒺藜这两个字,就不由心生怨恨,莫名惧怕,恨不能将其斩草除根,让它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主要源于无数次挨过蒺藜果实的扎,蒺藜果实扎手扎脚,也扎自行车磨得溜薄的车胎,害得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推着没气的车,最远走过十几里路。每次割草只要发现蒺藜的踪影,我都会疯狂报复,挥舞镰刀一阵乱砍,看到蒺藜的藤蔓七零八散躺满一地,才算解了心头之恨。
对于蒺藜的态度,我的祖母和母亲却和我不同,她们每年秋天都会从地里薅一捆带根的蒺藜,晒干后挂在房檐下的木橛上,留作药用。我的祖母、母亲,还有村里那些大娘大婶们,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几个字,但她们熟稔各种中草药的习性和用途,靠着蒺藜、灰圪针、茵陈之类的野草,医治了一家老小的病痛。
祖父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没有念过几天书,却极爱看戏、听坠子书。祖父说,可别小看这蒺藜,旧时候打仗,可是立过大功的。祖父告诉我,三国时期,诸葛亮根据蒺藜果实特点发明了蒺藜阵,对步兵和骑兵的杀伤力最大。我着实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小小蒺藜,它的故事居然还充满刀光剑影。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