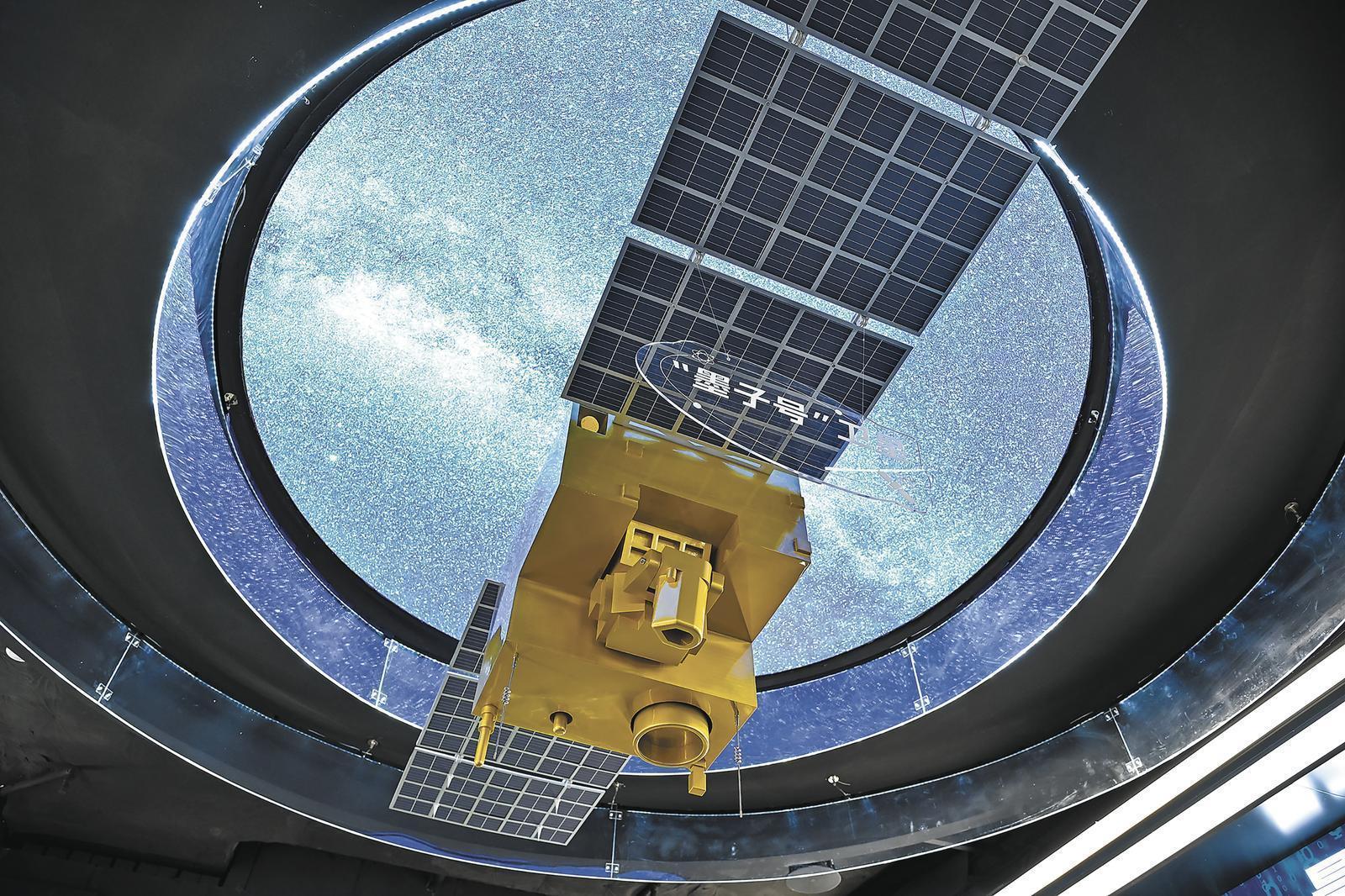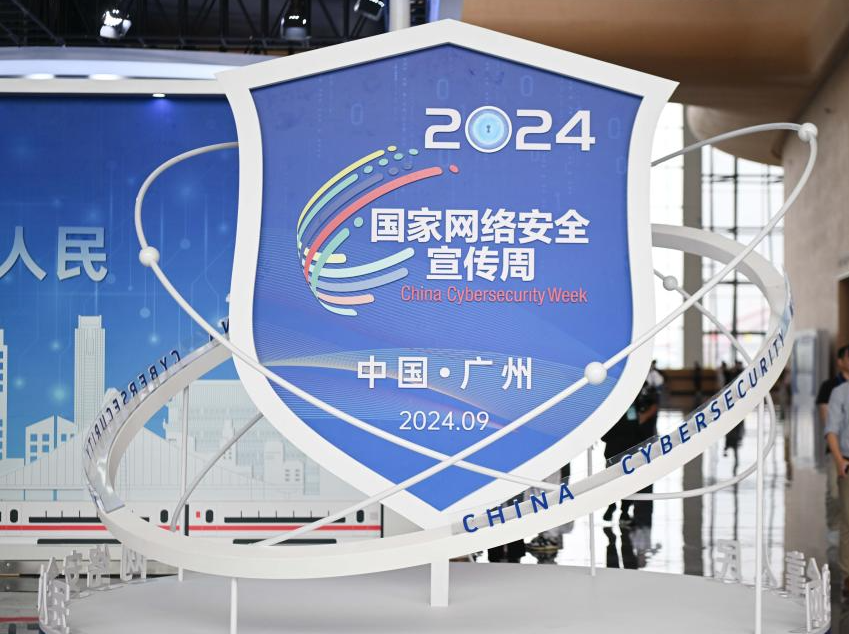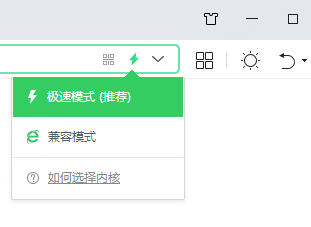从世界屋脊到南极冰原,从奥运赛场到“蛟龙”母船,从地震废墟到大科学工程现场……四十年来,科技日报记者始终奔走在新闻一线,用笔和镜头记录时代变迁与科技发展。
值此《科技日报》创刊四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回望曾经经历的新闻现场,重温采访时的燃情瞬间。

把文章写在世界屋脊上
罗晖 游雪晴
“我深深眷恋着青藏高原,‘想念’不够劲儿,离不开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91岁接受采访时,用不太“科学”的语言表达了他对那片土地的强烈情感。在那里,一代代青藏科考人,风餐露宿、爬冰卧雪,用青春甚至生命把论文写在了世界屋脊上。
对那片土地,记者同样深深眷恋。因为曾有幸和他们在一起,写他们的故事,学他们的精神。而“在现场”的获得感,是对记者这份职业的最大奖赏。
2005年,在孙鸿烈的关心下,一场规模浩大的珠峰地区多学科综合科考启动。作为随队记者,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和科考队员在一起,驻扎在珠峰科考现场。
因为在现场,我们对高原反应和高原上的艰苦生活有了切身感受。在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头疼、气喘,永远无法一觉睡到天明。由于科研经费拮据,科考队员吃的是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儿,很少见到肉和青菜;喝的是绒布河里几乎没有过滤的水;住的是直不起腰的小帐篷,大帐篷只有两个,男女混住,晚上咳嗽声此起彼伏。这是我们的一个月,却是青藏科考人的日常。
因为在现场,我们常常被震撼。到珠峰的第一个晚上,刚刚从高山营地回到大本营的康世昌队长微笑着和我们握手,干裂的嘴唇渗出鲜血。而独自在高山营地待了50多天的丛志远老师胡子拉碴的,完全瘦脱了相。一次,我们跟着张镱锂老师去喜马拉雅南坡做样方,几十年前“老青藏”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度手绘记录的复印件是“指南”。一大早大家就在大约60度的山坡上攀爬、比照,终于找到了记录里的位置。忙完下山时,已是下午3点多。
因为在现场,我们收获了成长和感动。凌晨3点和科考队员一起放探空气球时,我们见识了夜幕中珠峰的巍峨;寻找冰湖的路上,我们听到了康世昌在“气短”的地方鼓舞士气的嘹亮歌声。那时候,珠峰大本营没有手机信号,我们与山下联系靠一部亚星电话。写时效性强的稿子要抱着电脑在刺眼的阳光下,找信号好的角度打电话念给同事。
临行前的那晚,结束采访已经是晚上11点,科考队员们都来与我们告别。科考队员们不善言辞,只是用歌声表达祝福,《送战友》《朋友》……一首接一首。那天的风有八九级,当歌声和着风声,飘荡在珠峰的夜空时,我们感觉,做记者,值了。
很庆幸,我们在现场,见证了“以大自然为实验室”的青藏高原研究发展历程上的重要一步。
从一次南极行到一生极地情
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2010年11月11日,作为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我搭乘“雪龙”号前往南极中山站。
地质调查是此次科考的重要任务之一。
南极大陆90%以上的表面终年冰雪覆盖,只有少部分在夏天“脱”去白色外套,露出黄色的岩石。虽然岩石上不长一草一木,地质工作者却将其称为“绿洲”。
为了寻找适合开展地质调查的“绿洲”,地质工作者王彦斌和仝来喜圈出了不少野外科考点。
有些野外科考点离南极中山站较远,得依靠直升机才能抵达,甚至还要在外宿营。2010年12月23日,我和王彦斌、仝来喜一行三人乘坐直升机去往Storoy岛(属于Bolingen群岛)。该岛与中山站直线距离虽然只有24公里,但岩石年龄跨度却以亿年计算。这也是其研究魅力所在。
到了目的地,王彦斌和仝来喜顶着强紫外线,踩着海冰,在岛上徒步穿梭取样,间或向我科普地质知识。临近中午,我们喝着白开水,嚼着从中山站带来的煎饼,乐在其中。结合这次采访经历,我撰写了长篇通讯《南极科考:追寻地球的“前世今生”》。
142天的南极之行,我撰写了70余篇、共计8万字的报道。这些报道有的是在数次晕船呕吐中完成的;有的是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冰盖上苦守得来的;有的甚至是冒着被冰裂缝“吞噬”的风险采写的。这些报道成为队员家属了解现场的第一渠道,更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窗——由此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极地人”,也有了和更多海洋人同行的机会。
一次南极行、一生极地情。愚钝如我,选择了以最笨拙的方式,在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中一路追寻,记录这段以极地行为起点的情缘。
2025年6月14日,我再次来到位于上海市曹路镇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码头,登上了刚从南极归来的“雪龙2”号,并邀请中国第27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领队、领队顾问出席我的《筑梦极地四十年》新书发布会。
都说新闻是易碎品,抚今追昔,我突然发现,有些当时不甚理解的事到了今天好像有了答案。从这个角度来说,经过时间的沉淀,当新闻变成历史,同样具有价值。而这,也许是给记者最珍贵的馈赠。
举起冬奥“飞扬”火炬
科技日报记者 魏依晨
2022年2月,根据报社安排,我前往河北张家口,进行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报道工作。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前一天,我接到消息,奥运圣火将在当日14时左右抵达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
当天,我中午12点便出了门,准备守在火炬手的必经之路上进行拍摄和采访。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天气里,我拿着摄像机在雪地里走了一个多小时,呼出的水汽在口罩上结成了小冰柱。为了保证顺利发稿,我将手机放到贴身的内兜里,不然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冻到自动关机。
火炬传递的时间一到,张家口赛区的第一棒火炬手便手持奥运圣火,从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北门的冬奥会倒计时牌处起跑。随后,我的镜头追随着一个个火炬手,成功记录了他们手持火炬奔跑、传递的画面。
奥运圣火在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站结束传递后,现场工作人员示意我们可以进行采访。看到几位火炬手已被媒体同行围住,我也挤了进去。
或许看到我对火炬很感兴趣,在采访的尾声,其中一位火炬手何岐兰主动问我:“小伙子,你要不要举一举?”
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兴奋地脱口而出:“好啊!”
接过沉甸甸的“飞扬”火炬,我的手臂竟有些微微发抖。
“来,小伙子,我给你拍张照片。”何岐兰接过我的手机说,“来,举高点!笑容灿烂点!”
“咔嚓!”快门声响起,我与奥运火炬的合照在此刻定格。
在“蛟龙”号上做“蛙人”
科技日报记者 付毅飞
2013年8月9日,我结结实实尝到了太平洋海水的滋味,满嘴咸涩,但心潮澎湃。
那一年,我有幸参与“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试验性应用航次第二航段报道任务。7月中旬,“蛟龙”母船“向阳红09”船出发,经过正在冒烟的帕干岛,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穿过常年信风带,于当地时间8月6日抵达位于东北太平洋的作业海域。第二天,“蛟龙”号顺利完成了该航段首次下潜作业。
我趴在母船护栏上围观“蛟龙”号回收,目光突然被“蛙人”吸引。由4人组成的“蛙人”小组,驾乘小艇从事着船上最特殊的工作:“蛟龙”布放时,他们负责解开主吊缆,守护它下潜;返回时,他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蛟龙”挂上缆绳,牵引它“回家”。我想:如果能登上小艇,零距离目击这个过程,一定很有意义。
2013年8月9日,“蛟龙”号再次下潜。下午5点,我穿上救生衣,戴上安全帽和手套,如愿成为“蛙人”小组第5人。
登艇时我遇到了麻烦。虽然天晴了,风浪却不小。我顺着挂在母船外的竖梯往下爬,上一秒明明已经踩到小艇,下一秒又与小艇相隔一人多高。最后我心一横眼一闭,找准节奏松开手,四脚朝天跌入艇中。见我笨手笨脚的样子,“蛙人”小组深感忧虑。小艇驾驶员张正云和组员张会生把我夹住,一左一右紧拽我的胳膊,我刚想说不用,一个浪劈头打来,话音伴着海水一起咽了回去,整个人从眼镜湿到袜子。
当“蛟龙”号浮出海面时,我们已经赶到它附近。“蛙人”崔磊一个箭步跳到“蛟龙”背上,利索地固定好龙头缆,又跳了回来,动作非常灵活。我们随即远远绕开。船员告诉我,如果被紧绷的缆绳抽到,别说血肉之躯,金属设备也照样打断。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海里还要戴安全帽。
回到甲板上,看到首次参与下潜的科学家正在被大伙泼水庆祝,嘴里又泛起了海水的味道。对我来说,那味道是“蛟龙”的回忆,至今难忘。
废墟上萌动春天的脉搏
科技日报记者 颉满斌
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兰州市震感强烈。19日凌晨4点,我了解到地震波及范围广、破坏性大,有人员伤亡,便立即向报社汇报情况,请求深入灾区采访。得到批准后,我驱车奔赴灾区。当天下午,在媒体同行的协助下,我进入受灾严重的积石山县大河家镇。震后的小镇满目疮痍,让我一时失语。短暂平复情绪后,我立刻拿起家伙事儿,投入到采访工作中。
大河家镇坐落在黄河岸边,是甘青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镇。我来到该镇的陈家村,发现村落因电力中断漆黑一片;在部分路段,电线因强震垂落在地上;部分房屋倒塌,碎玻璃、砖头、石块散落在街道上。
我在灾区不断穿梭,尽可能了解、记录实时情况。开阔地带临时搭建的帐篷内,被疏散的村民围坐在一起,身旁是食物和水等物资。帐篷外,应急救援车和救护车整齐列阵,救援人员和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地转移群众、救治伤员。在现场,我无时无刻不被当地群众的朴实与坚韧打动。灾难无情,人间有爱。震区之外,还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为灾区送来温暖和力量。
震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再次走进积石山。集中安置点井然有序,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大家围坐在灶台边,边包饺子,边聊着开春后的打算,眼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期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支援,让这片土地重新积聚起温度。春天的脉搏,已在冻土之下悄然萌动。
追逐“幽灵粒子”的踪迹
科技日报记者 陆成宽
中微子又称“幽灵粒子”,可轻易穿透万物而不留痕迹。
我曾两次到中微子实验现场采访。第一次恰逢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以下简称“大亚湾实验”)装置退役之时。
那一天是2020年12月12日。当天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下面,我们停止大亚湾实验的取数运行。”说完,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便按下了停止运行的按钮,屏幕上的数据随即停止跳动。之后,实验大厅的水池外罩缓缓打开,沉浸在碧蓝色高纯水中的四个中微子探测器,徐徐展现在众人眼前。
大科学工程在达成目标后主动退役,并不常见。在现场,我问王贻芳:“为什么选择让大亚湾实验装置退役?如果继续运行下去,是否还可能获得新的发现?”
他立刻给出了明确而坚定的回答:“大亚湾实验已运行九年,它的核心科学目标全部完成,对中微子振荡振幅的测量精度也已达到极限,不可能再提升。继续运行不再具有科学价值,只会浪费资源与时间。”
大亚湾实验虽画下了句号,但这并不是我国中微子研究的终点。
2025年11月19日,我再次来到中微子实验现场。巧合的是,这一次恰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宣布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建成。
当天,王贻芳带领记者团从地面入口出发,登上了通往地下的“小火车”。列车沿斜井隧道缓缓下行,鼓风机持续轰鸣。约15分钟后,我们抵达了位于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现场。
与先前的大亚湾实验相比,江门中微子实验的规模要庞大得多。在现场,我们先后参观了井下冷冻泵室、液闪灌装间、实验大厅等场所。
王贻芳边走边介绍,不仅解释各处设施的功能,还会用生动的语言介绍探测器“眼睛”的工作原理,以及实验为何要建在地下700米等。
当我们乘坐“小火车”离开实验大厅,重返地面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五年前大亚湾实验停止运行后,那碧蓝色水池外罩缓缓打开的一幕。
从大亚湾到江门,从退役到新生,中国的中微子研究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接力。王贻芳和他的团队,正如一群在地下最深处布下天罗地网的猎手,执着地追逐着“幽灵粒子”的踪迹,探寻着宇宙最深处的奥秘。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