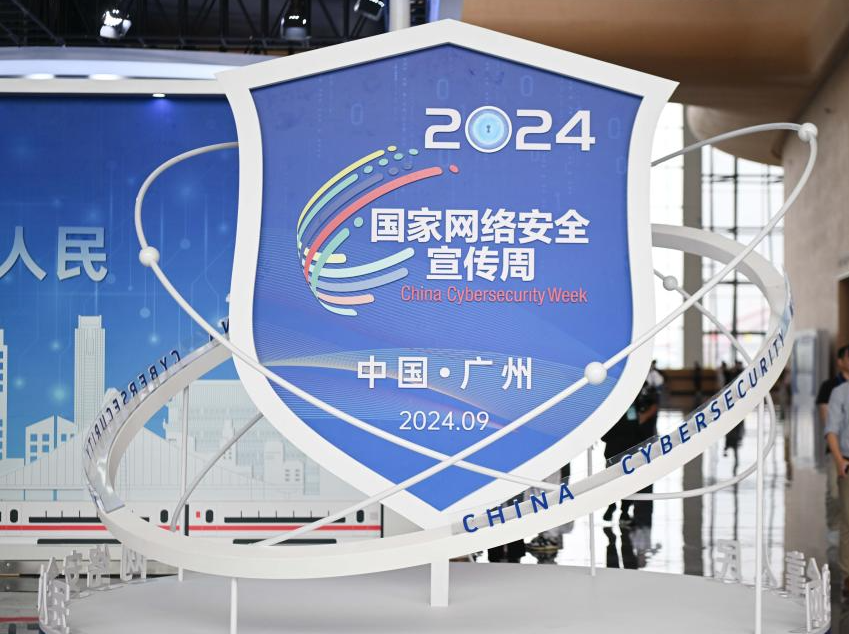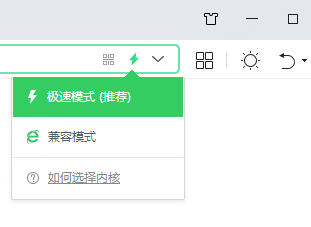我采访钱三强,是从一封信件开始的。
1988年初,钱老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仍然事务繁杂,约访难如登天。为此,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明采访意图——聚焦他在法国居里实验室的十年成长历程,展开报道。为了便于他了解我,我还把自己以往撰写的茅以升、杨乐等科学家的作品一同寄了过去。没想到过了一阵子,他的秘书回信了,约定每周抽半天时间,在中国科学院的办公室里跟我畅谈。
我没有上过大学,仅拥有中学阶段积累的一点物理常识。尽管采访前做了不少准备,但第一次交谈时,诸多地方仍似懂非懂。临别时,钱老递过来一摞材料,其中《科坛漫话》一书格外显眼,里面那篇《原子史话》被他特意折了角。回到家后,我将这篇文章连读三遍,待第二次见面,我已能顺畅地跟上他的思路。就这样,我们从他在清华大学的读书时光,聊到居里实验室的清晨,再聊到核物理研究中的困境。我们一谈就是五个半天,每次三个多小时。随着对话的深入,我仿佛也经历了他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一步步成长为科学家的那段时光。
当我整理完笔记准备动笔时,却犯了难。面对钱老厚重的科研人生,我竟一时不知如何下笔,甚至生出了稿子要“砸锅”的焦虑。梳理出写作提纲后,我发现钱老前五次谈话中从未提及“三分裂”成果,但这恰恰是他科研生涯的核心成就。于是,我将提纲与补充采访的请求一同写信寄给了钱老。他看后手写了几十页的详细材料,完整阐述研究始末。随后我们又畅聊了两次,这让我意外又感动。
写作过程中,我仔细揣摩如何平衡新闻性与科学性,避开复杂的技术细节,着重挖掘背后的科学思想与精神——写他“立足常规,着眼新奇”的科研理念,写他重视动手能力的实践态度,写他不唯名家、坚持真理的治学品格。通过吹玻璃、做实验等典型细节,我力求既能让读者看懂,又能从中汲取力量。
初稿完成后,钱老很满意,只在技术细节上补充了两百字。他还特意从家里翻出一叠发黄的老照片,让我拿去登报。其中,有他与居里夫人在实验室外的合影,还有夫人何泽慧年轻时梳着小辫的模样,一张张都承载着珍贵的回忆。这份信任,如暖流般淌过我的心底。
1988年2月23日,《通往科学家之路》在《科技日报》刊登,很快在科技界传开。后来,钱老还特意把我翻旧的《科坛漫话》题上“纪念我们愉快的合作”送给我,又补了本崭新的签名版给我。
1992年,钱老去世了,但这份情并未终结。多年后,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周年座谈会举行,何泽慧推掉了中国科学院的会,专程来参加。那天,她还受了伤,胳膊用绷带吊着坐在主席台上。她专门带了一本新出版的《钱三强文集》,上面题写着“送给郭梅尼同志”。科学家这样的认可,是对记者的最高奖赏。
(科技日报原记者郭梅尼口述,科技日报记者荆晓青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