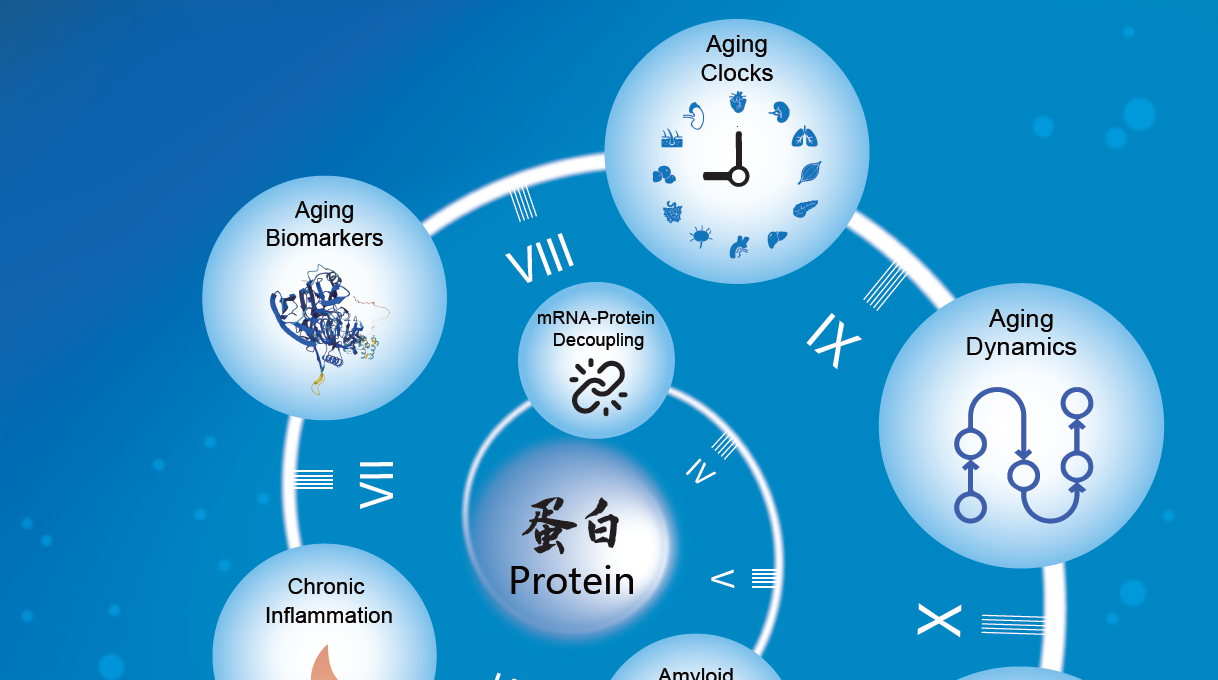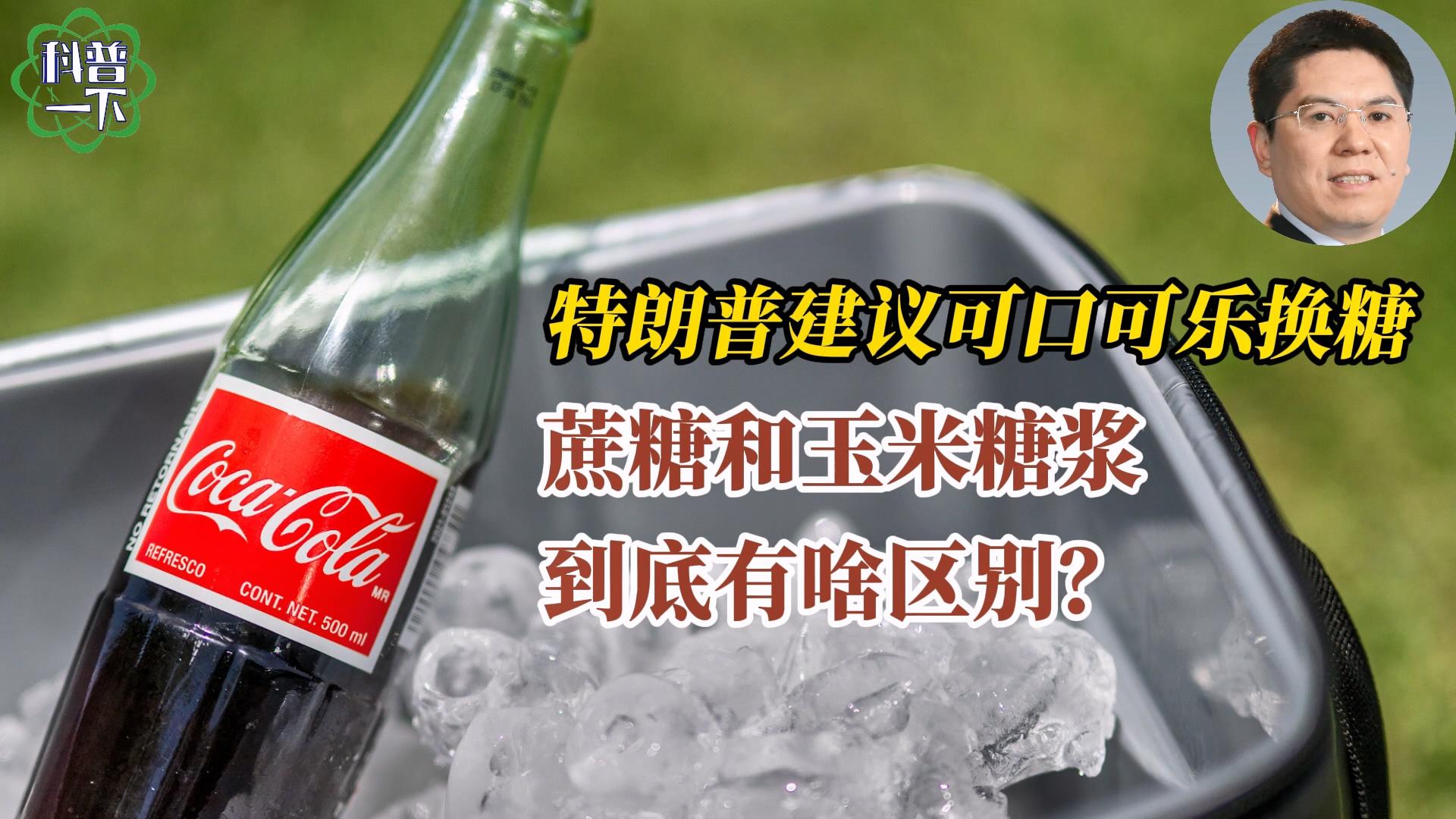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代小佩
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地衣这一特殊生物复合体,曾长期处于我国科学家的认知之外。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衣真菌学家魏江春经过半个多世纪深耕,用智慧和坚持在地衣学领域取得系列成果。
魏江春是中国地衣学科的开拓者。从零起步,他建立了亚洲最大的地衣标本室,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衣型真菌全基因组测序及其基本生物学分析,从中发现大量抗逆基因和“沉默基因”,并破解其激活机制;他提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为治沙提供新路径。魏江春推动中国地衣学科完成了从“一人独行”到“世界领跑”的跨越。
魏江春的科研足迹,勾勒出地衣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更展现出中国科学家填补学科空白、勇攀世界高峰的精神力量。
前不久,魏江春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专访。从地衣的本质特性到其科学价值,从个人科研历程到学科发展脉络,94岁的他娓娓道来我国地衣学科发展的历程。
白手起家建立亚洲最大地衣标本室
记者:您投身地衣研究已70余年。很多人对“地衣”并不熟悉,能否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一下什么是地衣?它的科学研究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魏江春:地衣是一类特殊的生物复合体,由真菌与光合生物(如藻类)共生形成。真菌通过菌丝为藻类提供水分、矿物质和物理保护,相当于为藻类“搭建房子”;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制造有机物供给真菌,如同为真菌“提供食物”。这种共生关系让地衣能在高山、极地、荒漠等极端环境中生存。
地衣的科学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
第一,它们是生态学上的“开路先锋”。地衣分泌的地衣酸能分解岩石、促进土壤形成,是裸岩、火山岩等极端环境中“生态演替的起点”,为后续动植物定居奠定基础。比如极地苔原中,地衣是重要的初级生产者。
第二,它们是环境监测的“天然指示剂”。其种类、分布和生长状况可反映空气质量。例如,“松萝”等树生地衣的消失,常常提示大气污染严重。
第三,它们是生物活性物质的“资源库”,约80%的地衣含独特次生代谢产物,具有抗菌、抗病毒、抗氧化、抗肿瘤等活性。此外,地衣还是研究生物进化与共生机制的理想模型,其标本对极端环境适应和气候变化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记者:您曾建立亚洲最大的地衣标本室,能否介绍一下它的规模和建设历程?
魏江春:1958年,我受时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戴芳澜委托,前往苏联学习地衣专业。当时,我国地衣学科还是一片空白。1962年,我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工作。1973年,我们正式建立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那时标本馆中的地衣标本室仅有一间房子,房间中仅有三个木柜。经过数十年积累,如今,中国科学院菌物标本馆收藏的地衣标本已超过16万号,拥有亚洲最大的地衣标本室。这个标本室不仅是我国地衣研究的物质基础,也为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支撑。
记者:在您发现的众多地衣标本中,哪一个最令您难忘?背后有怎样的科研故事?
魏江春:1989年,腾格里沙漠东南沙坡头地区治沙站站长给我来信,称1956年植树造林治沙的植被盖度由25%下降至6%,当地沙漠结皮盖度由0%变成90%。他猜测这种数据变化与地衣的生长情况有关。我前往当地考察后确认了这一发现,并确定产生影响的地衣中,优势品种是石果衣。这个发现的意义远超预期。
我们对石果衣的真菌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时,在从来都不产生次生代谢产物的石果衣真菌全基因组中发现了“沉默基因”——这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沉默基因”如同“沉睡”的资源,不参与次生代谢产物的合成。一百多年来,学界研究地衣代谢产物时,从未意识到未产生活性物质的地衣中还存在这类基因。
我们尝试通过培养,激活了其中16种“沉默基因”,最终使石果衣产生了17种以上的次生代谢产物,其中多个为新结构。这一突破证明,通过激活“沉默基因”,可以让不产生和少产生次生代谢产物的地衣释放大量潜在的天然产物资源。这一发现为药物研发等活动开辟了新路径。
首次提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
记者:您提出“沙漠生物地毯工程”的概念,其核心依据是什么?这一工程对治沙有何意义?
魏江春:核心依据是我对前述沙坡头地区的结皮生物石果衣进行的研究。我们将石果衣制成粉末悬浮液,在纯沙上进行接种实验。实验发现,在1平方米的区域中,接种石果衣的部分在一年半后形成了结皮,未接种的部分仍为沙漠。这表明,地衣能在极端干旱环境中形成稳定表层,发挥防风固沙作用。
沙坡头地区年降水量仅200毫米,蒸发量却达2000毫米,传统种树治沙方法可能像“抽水机”一样消耗地下土壤水分,加剧干旱。而地衣等结皮生物形成的“生物地毯”能稳定沙漠地表,且无需大量消耗地下土壤水分,可以更好地适应干旱、盐碱等极端环境。因此,“沙漠生物地毯工程”为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生态修复提供了更可持续的方案。
记者:如何证实“沙漠生物地毯工程”的可行性?地衣的抗逆基因在农业领域有哪些应用?
魏江春:我们通过基因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其潜力。石果衣等沙漠地衣含有丰富的抗干旱、抗盐碱基因,我们选取其中7个基因,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导入牧草和紫花苜蓿,显著提升了这些植物的抗逆性;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聊城大学合作,将抗逆基因导入小麦、玉米、水稻,也使作物的抗旱、抗盐碱能力明显增强,相关成果已申请多项专利,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实践证明,地衣抗逆基因能有效改良农作物和牧草的适应性,而“沙漠生物地毯工程”不仅能固沙,还能为极端环境下的生物修复提供基因资源支撑。
记者:1958年您赴苏联学习时,我国地衣学科还是空白,如今已实现领跑世界。在实现这一跨越的过程中,我国地衣学科取得了哪些标志性成就?
魏江春:中国地衣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填补空白,从无到有建立研究基础;第二阶段是追赶前沿,缩小与国际前沿水平的差距;第三阶段是创新领跑,目前在多个领域已实现世界领先。
例如,我们完成了地衣领域首个全基因组测序,揭示了“沉默基因”的存在及其激活机制,这一成果被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编辑评价为“真正的地衣学基因水平研究突破”。
此外,在沙漠地衣生态应用、抗逆基因挖掘、地衣标本库建设,以及地衣生物学科教等方面,我国也已拥有一批优秀的科研单位和人才,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学科影响力显著提升。
保障科研人员做到“安钻迷”
记者:从“一个人的学科”到形成完整团队,您在推动中国地衣学科发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魏江春:初期的困难主要来自物质条件和人才的匮乏。我从苏联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人战斗”。家人远在西安,我独自在北京开展研究,生活十分简朴。由于长期在食堂吃饭,以至于后来闻到食堂饭菜的味儿就有些反胃。但支撑我坚持到底的,是“让中国地衣学科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信念。
地衣研究在国内曾不受重视,获取经费、组建团队都面临阻力。比如,早期采集标本需深入荒漠、高山等极端环境,交通和设备条件有限,常需徒步跋涉;实验室建设也需从零开始,一步步积累仪器和样本。但这些困难都在“填补空白”的目标驱动下逐渐被克服。
记者:如今中国地衣学科队伍已颇具规模,能否介绍一下团队建设的现状?
魏江春:从1973年建立地衣标本室开始,团队逐步壮大。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衣科研工作站。27所大专院校开设地衣专业,共有38位研究人员和51名正在学习的研究生。我培养了37名硕士、20名博士和3名博士后,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梯队。这些人才在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继续深耕地衣分类、生态、物种、基因等领域,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例如,我指导的博士钱旭从事世界领先的地衣抗逆基因资源创新利用研究,我觉得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我十分关心他的事业发展,希望他能继续深入做这方面研究,取得更大成绩。
可以说,中国地衣学科已从“一人独行”走向“众人接力”,研究范围也从基础分类拓展到分子生物学、应用技术等多个方向。
记者:您认为推动地衣学科人才队伍建设,当前最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魏江春:核心是让科研人员能做到“安钻迷”——安心、钻研、入迷。我认为,科学家只有不轻易受外界琐事干扰,才能够专注研究、全身心投入,钻研科学到入迷的程度,如此才能出成果。要让科学家安心,需要为他们提供稳定的科研环境。
但现在的科研人员很难做到“安钻迷”,因为他们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解决实验室房租、团队工资等行政事务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理顺管理机制,为科研人员“减负”,让他们能安心投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