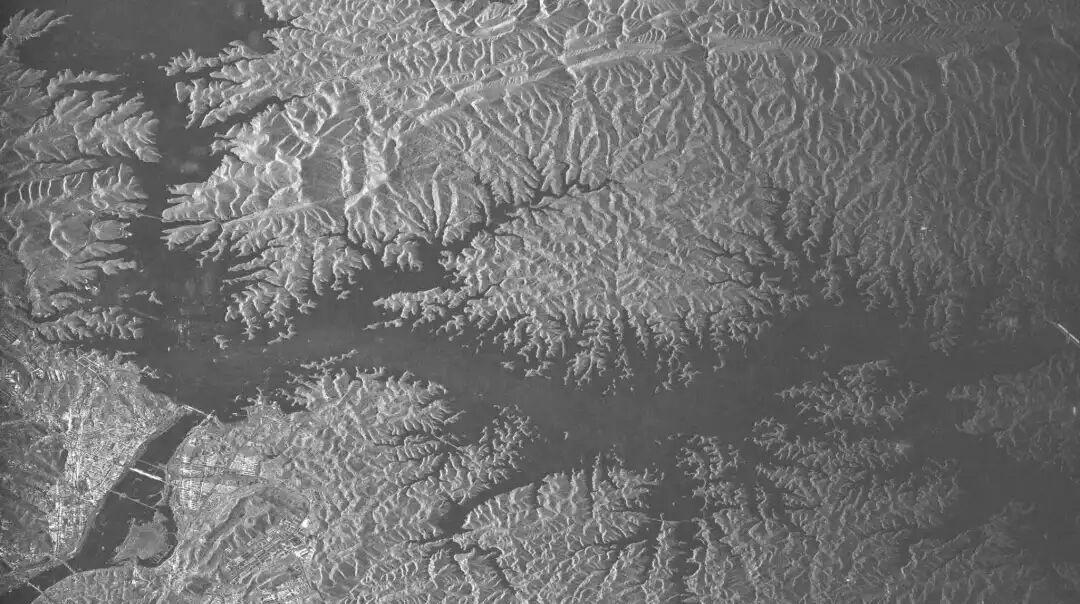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策划 刘恕 李坤
浙江省嘉兴市省身教育集团科学老师钱嘉彧开着车,把他的宝贝“教具”从浙江嘉兴一路拉到了江苏苏州,拉到了第二届科学教育支持计划展示活动的现场。

那是一棵带枝丫的从底部到树梢所有部分完整保留的树。钱嘉彧在树的不同部位进行了切片,给每个切片都标上了编号,还用砂纸细细打磨,让切片上的每一圈年轮都清晰可见。
围绕这棵树,钱嘉彧给孩子们上了一系列主题为“年轮”的科学课。课程得到小学特级教师、桂馨科学课项目首席专家章鼎儿的高度评价。因为,孩子们在课堂上提出了可探究的好问题。
科学教育支持计划由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和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共同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具有改革、研究和创新价值的小学科学教育教学研究和实践成果,并举办展示活动,以此激励一线教育工作者投身小学生科学启蒙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工作。
科学课“年轮”就是此次得到支持的成果之一。
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答案
2017年,钱嘉彧所在学校校外进行道路改造,不少树枝被修剪。他敏锐意识到,这是让孩子研究年轮的绝佳“教材”,干脆拖了一段树枝回学校。
他至今还保留着用那段树枝做的年轮切片。切片上,环形纹路一圈套一圈,有的紧密,有的稀疏;有的地方宽,有的地方窄。
教科书上说,年轮的凹凸方向和疏密分布,会受到光照和水分的影响。
但究竟是不是这样?钱嘉彧发现,学生其实无法验证。就算得出所谓的结论,也不过是根据课本知识反推。
孩子无法围绕它真正展开探究,这个“教具”还不够理想。
钱嘉彧只能继续寻找。
行道树死掉后,园林部门会将它们统一运到特定地方处理。钱嘉彧开车从市区过去,要花一个多小时。

他找了好几次,终于捡到了一棵理想的香樟树。
树有些长,钱嘉彧先在现场用锯子把树切成几段,做好记号,塞进后备箱;拉回学校仪器室后,再等上一个月,让它充分干燥;最后在树的不同部位“下手”,制作年轮切片。
“从切片里能看出很多东西!”钱嘉彧像展示宝贝一样拿起一块切片——上面赫然是两个并排的同心圆,代表着两根枝杈在此分开、各自成长。“同学们看到后,非常惊喜。”钱嘉彧说,在各种教科书上,都没有这样的示意图。
树成了最好的老师。

钱嘉彧已经教了9年科学课,越教越品出其中的味道。一开始,他觉得科学课是教知识,后来他意识到,科学课教的是方法,是素养。
章鼎儿认为,单纯教知识的科学课,已经到了被淘汰的边缘。让孩子读关于年轮的绘本,看关于年轮的视频,获得的知识量都比听老师上一堂课更多。“我们要从知识教学层面的课中走出来。”章鼎儿说,跨出这一步,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让学生学会提问。
传统“年轮”课上,孩子一般会问,树的年轮为什么有一圈圈的纹路,为什么圈纹有深有浅,为什么宽窄不一……
章鼎儿认为,这类问题是原生态、浅层次的,“幼儿园的孩子也会问”。问题是问别人的,问题一提出,思维活动就停止了,进入了被动等待答案的状态。这样的课堂看起来非常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但接下来呢?接下来只有一条路,老师告诉学生答案,重回教知识的老路。
“提出一个自己可以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孩子欠缺的能力。”章鼎儿强调。
钱嘉彧的“年轮”课上,学生会问这样的问题:树干的每个部位都有年轮吗?树干基部、中部、顶部的年轮圈数是一样的吗?
寻找答案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学生只需要观察比较钱嘉彧带到课堂的树,就能得出结论。他们发现,要知道一棵树的年龄,应该观察树干基部的年轮;如果只观察一个切面上的年轮,知道的只是这根枝杈的生长年龄。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意义非凡。课堂上,学生自主经历了一个科学探究活动过程,经历了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章鼎儿说。
走出“年轮”的课堂,孩子还可以研究叶片,研究石头,研究花朵。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提问,如何观察,如何探究。
将实践能力纳入测评
科学课一直倡导探究式教学,但据老师观察,学生仍然缺乏科学探究的意识和探究实践的能力。
原因之一,可能是科学课上可供学生探究学习的材料有限。
多位一线科学老师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上课的一大难题,是缺少配套实验器材。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凯瑞小学科学教师张建晓笑着说,她就像个收破烂的,收瓶子,收气球,收蜡烛,“手搓”各种实验教具。
为了演示空气的热胀冷缩,张建晓从学校接待室借暖瓶,带洗手液和色素配置泡泡液,给学生变“吹泡泡”的魔法;为了模拟热气球的升空,她用瓦楞纸和透明胶做了十来个和酒精灯配套的筒,在筒底剪出几个小缺口,让放在酒精灯上的塑料袋能晃晃悠悠飘起来;为了演示太阳和影子的概念,她用一次性纸杯、彩色马克笔和静电膜制作旋转投影仪,探索多次后发现,静电膜比透明胶和保鲜膜都好用……
“为孩子多做点儿,我不怕麻烦。”张建晓说。
当然,在有些地区,实验器材不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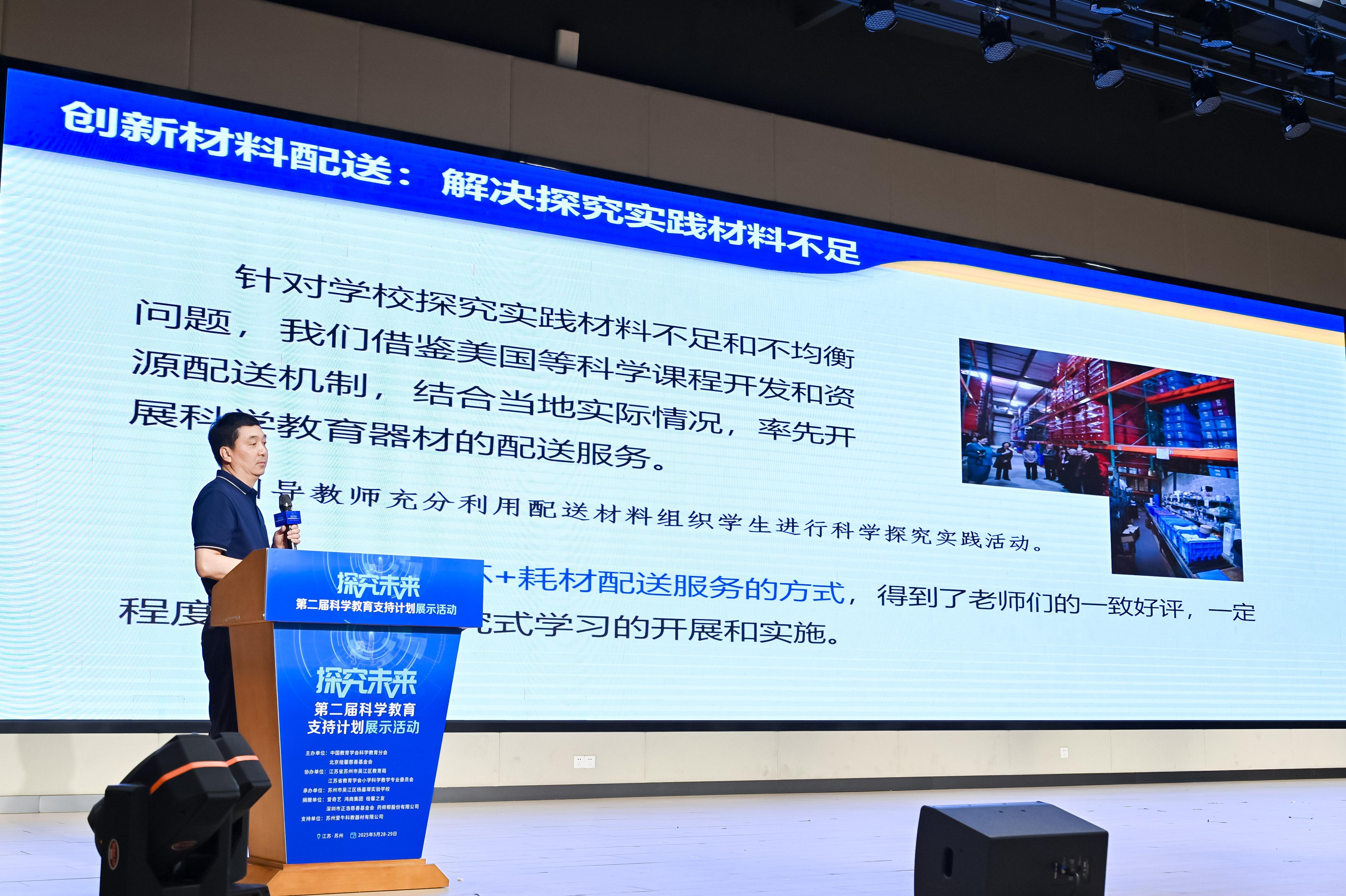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小学科学教师兼教研员姜向阳介绍,他们借鉴发达国家科学课程开发和资源配送机制,早在2010年就实行了科学课器材的配送服务,以“工具箱+耗材包”的形式将所需器材配送到各个学校。
但即使有器材,科学课也无法顺理成章地变得“可探究”。
有科学老师问:“我要是带孩子做实验、搞探究,他们背概念和做题的时间就少了。但我们期末考试都要做题呀,这搞得我很苦恼。”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区的科学课测试为纸笔测试,侧重对知识点的考察。如果要追求高分,教师选择以阅读和记忆为主的方式授课反而更出成绩,还出现了专职科学老师教不过兼职老师的“怪现象”。
“改变评价指挥棒,才能改变课堂。”姜向阳分享了滨江区的做法——改革期末测评内容,把探究实践能力纳入科学课期末测评。
但新问题又来了。这种测评苦了阅卷老师:考完试后,要把实验装置一个一个装箱,整箱整箱运到区里的教研中心;阅卷时要一箱一箱拆开,一份一份拿出,一个一个操作……
评价过程耗时耗力。一次期末考试,全区科学老师上阵,完成一个年级的阅卷也要用上足足两天。
评阅的问题不解决,实践导向的测评方式就难以为继。
姜向阳介绍,从2019年开始,区里利用数智技术构建了科学探究实践能力智评系统,搭建了精准、高效、便捷的数据收集、处理和反馈的智评平台,用于测评学生探究实践能力。
小程序拍摄、上传学生实践作品,数据采集终端批量上传学生答卷,老师不用一次次装箱再拆箱了,可以在移动端或者电脑端上阅卷,还能实现多端共联、多位老师共同评议。
阅卷变得高效了,阅评完成后,系统还能对学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和整理,帮助老师改进教学。
姜向阳说,这种指向探究实践能力培养的智评体系,帮区域的科学课实现了“四个转变”:培养目标从分数导向转向素养导向;教学内容从以科学知识为主转向科学知识与实践能力融合;教学方式从以教为主转向以学为主;教学评价从以结果评价为主转向过程和增值评价结合。
切实优化课堂设计
一批科学老师已经行动起来,尝试让科学课变得更好。
那么,什么是好的科学课?
很多老师和专家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科学课的好坏,要看学生的状态,看学生是不是得到充分调动,能不能积极参与课堂。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数字教育研究所评价教研员单道华说,在科学课上,学生要有所得。这个“得”不是说获得了多少科学知识,而是有没有了解科学方法、科学本质,有没有燃起科学兴趣。她表示,在小学阶段强调知识考核并无太大意义,更应让孩子有机会获得实践经验,特别是直接的、切身的体验。
在实践当中,素养才会慢慢形成。科学老师必须做好课堂设计,“钩住”学生,还要进一步启发学生。
不过,能不能把课上好,自主权未必完全掌握在科学老师手中。单道华提醒,课堂的教学方式,会受到学校和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理念的影响和限制。“上好一堂科学课,也需要一整套配套机制支持。”她说。
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省缙云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陈志强坦言:“我们的科学课还没有达到一些老科学教师二三十年前就提出的‘走向探究’的水平。”
参与起草了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小学自然课教学大纲的著名科学教育家刘默耕,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积极在小学自然课教学改革中推广实验“探究—研讨”教学法,强调探究过程与科学思维训练。
时间走到今天,《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探究实践”一词取代了之前的“科学探究”。新课标强调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基于探究问题,经历“从未知到已知”的探究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习得技术运用的意识与能力。
陈志强认为,课堂有没有走向探究,可以从几个直观“指标”上来观察:一是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看学生有没有主动参与课堂活动;二是看学生活动自主性,有没有得到比较长的思考时间和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三是看有没有真正的交流研讨,是单纯地汇报,还是彼此之间有火花和碰撞。“我们一定要清楚科学课上设计一系列活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传授知识,还是为了发展素养。”陈志强说。
“在一堂课上,学习内容宜少不宜多,可以只解决一个问题,研究一个主题。”湖南省芙蓉教学名师孙江波建议,课堂上深挖一个问题,能让学生“真思考”“真研究”。
他还建议,老师可以给每堂课的学习方法都设置一个重点。例如这一堂课,侧重于让学生提问;下一堂课,侧重于让学生观察和测量;再下一堂课,侧重于让他们进行信息的处理和分析……
“我们要从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出发,明确为什么而教。孩子的学习是为未来而学的,最终要走向跨学科、综合性学习。因此,要下功夫研究怎样的教学方法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孙江波强调。
章鼎儿观摩指导过很多科学课。他坦率地表示,当下上的课,并非真正的科学课,而是需要经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前科学课”。
“我们希望科学教育支持计划,能支持肩负这场变革任务的改革者、先行者、全新科学课程的建设者。”章鼎儿用沉静的语调说道,“他们就在我们这支数以万计的科学老师队伍之中。”
【记者手记】
小课堂中的大门道
张盖伦
早在今年3月份,桂馨科学课项目的两位专家章鼎儿和刘晋斌就特意从杭州来到北京,为入围第二届科学教育支持计划的课程“磨课”。
章鼎儿已80多岁,刘晋斌也已年过花甲,但他们为了年轻科学老师的课程,甘愿在全国各地奔波。
“磨课”,也就是指出教师课程中有待商榷的部分,大家共同探讨能够如何改进。
其中一堂课,是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科学老师的“认识其他动物的卵”。
教材上鼓励研究蚕宝宝的卵,但蚕卵太小了,很难观察。老师想了一个办法——先观察鸡蛋,也就是鸡的卵。鸡卵从外到里有卵壳、卵壳膜……蚕卵会不会也有类似的结构呢?这下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不同动物卵的结构是一样的吗?于是,还要研究其他动物的卵。老师又找了好些其他动物卵的视频,让学生认知其中的相同与不同。
这堂课很有想法。章鼎儿说,科学课本身就要求孩子养蚕,那么孩子天然会对蚕卵感兴趣,但是观察蚕卵,会遇到困难。他最欣赏的就是,当遇到困难时,老师鼓励孩子们想办法,用观察鸡卵来“曲线救国”。“这就从原有框架里跨出了有价值的一步。”章鼎儿表示。
之后,专家和学校教研组的老师们讨论起了课程板书。在我看来,那是逻辑非常清晰的板书,能让孩子认知卵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
但他们有更多考量。
“这种板书当然有好处,可以帮助孩子整理归纳,降低思维难度,但缺点是会限制孩子的思维。”“说对了就写一条板书上去,我们老师经常这么做。但这样一来,孩子可能就去猜老师想要的答案是什么,反而未必真正经历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认知过程。”两位专家说。
“我也常常在想,一节课的目的是什么。是把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全部提炼出来告诉学生;还是重在让他们感受,把提炼放在日后进行?”在场的年轻老师提出自己的困惑。
他们七嘴八舌,我边记录边感叹:原来板书里的门道也这么深。
章鼎儿鼓励参与“磨课”的所有老师都畅所欲言。“你不要觉得提出问题是批评,恰恰相反,提出问题是对一堂课最大的帮助。”他说,老师想上好课,就一定要发现问题,总结经验,一轮轮迭代,课才能往前推进。
是啊,小小一堂课有大门道,小小一堂课也能带给有心人许多思考。老专家和年轻科学老师的认真,都让我感动。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科学课也承担着教育改革的使命。大家付出如此多心血,无非就是为了把一堂堂课上好——理念如此朴素,价值又重逾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