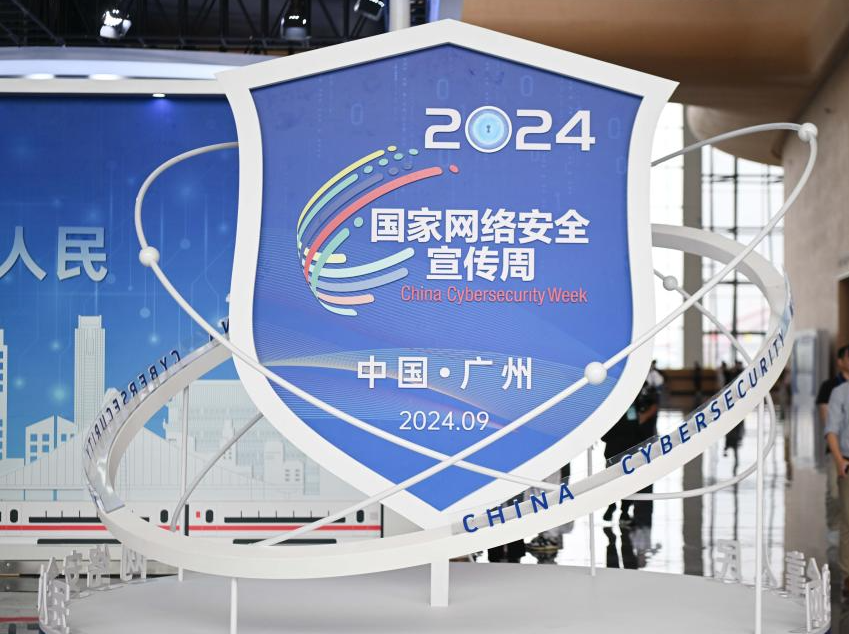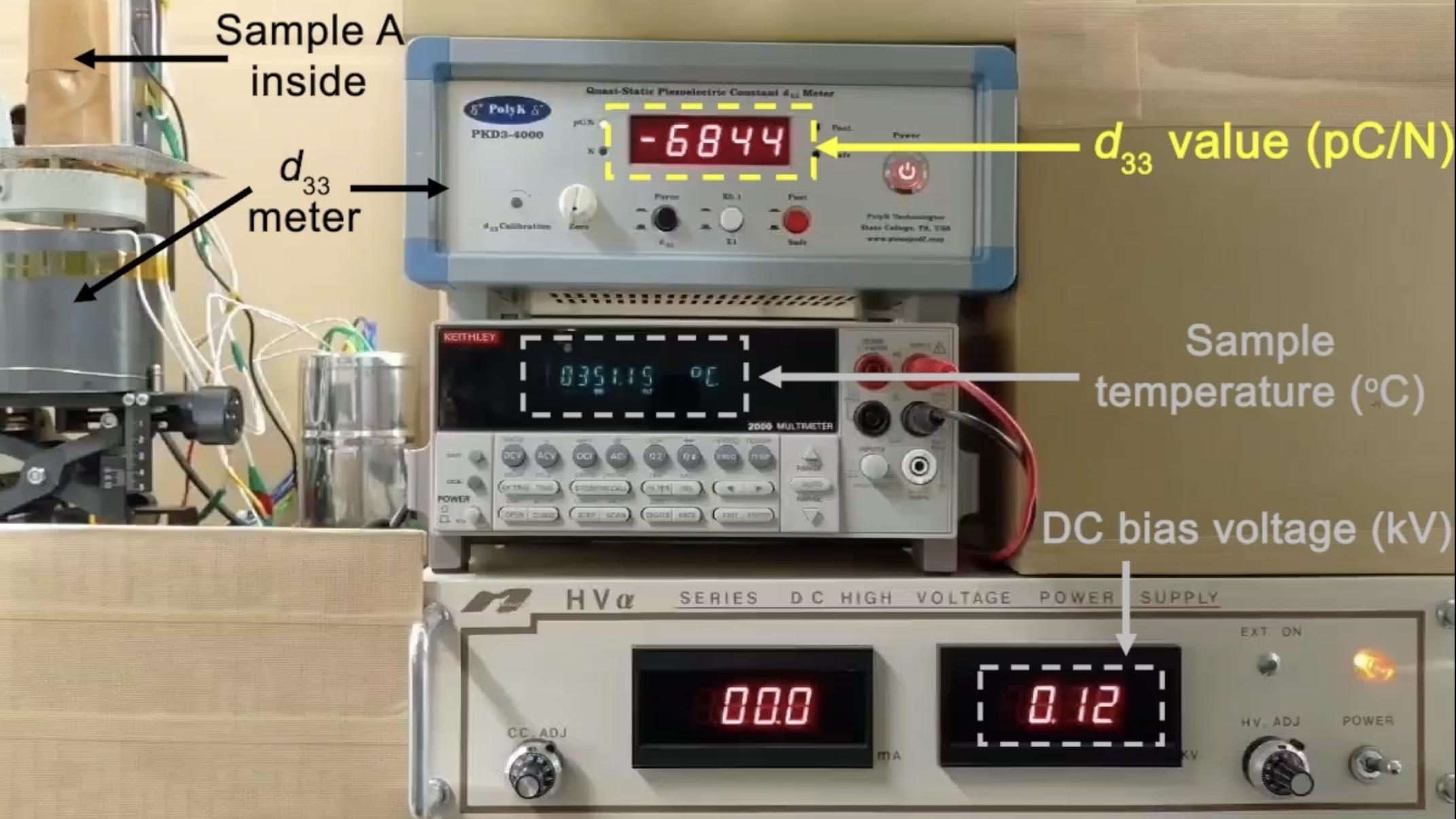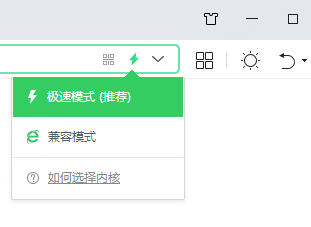科技日报记者 王延斌 通讯员 林萍 赵英佐
无影灯下,中国工程院院士、眼科学专家谢立信全神贯注地看着患者的眼球,0.5毫米厚的角膜之上,手术刀如同加了高清导航般精准地移动。可以说,手术中的谢立信“手稳如机械臂,眼利似显微镜,心细如计算机”。
前不久,谢立信获得2025年度吴阶平医学奖。
牵头创建集科研、医疗、教学于一体的国家级眼科中心,率先将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引入国内,在角膜病基础研究、角膜替代材料及人工角膜研发上取得一系列原创突破……谢立信的人生轨迹,与我国现代眼科学从追赶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发展历程交织。
1月上旬,在繁忙的主刀手术间隙,记者专访了这位年逾八旬仍坚持手术、门诊、教学的“追光者”,聆听他关于初心、攻坚、育人以及学科未来的思考。
从国家和患者最急迫的需求出发
记者:您当初为什么选择当眼科医生?
谢立信:我1965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潍坊医学院。开始时,我做了一年多的妇产科医生。由于包括妊娠高血压疾病等在内的许多妇产科疾病与眼科有关,我被安排去眼科学习一段时间。眼科主任看好我,把我留了下来。我当时主要从事角膜病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工作,而之所以选择角膜病这个又难又不容易出成绩的专业,主要是因为患者需要。
感染性角膜病是重要的致盲性眼病,其中真菌性角膜炎尤为常见,多由植物性外伤引起。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在田间劳作时,眼睛极易被植物划伤,一旦发生真菌感染,往往面临严重的视力损害甚至失明。作为一名医生,面对大量因角膜病而失去光明的患者,我深感触动。科研选题从国家和患者最急迫的需求出发,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性。后来,白内障成为主要致盲眼病,我又投身其中,率先将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引进国内并推广。
记者: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眼科医疗是什么状况?
谢立信: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六十年前的情景,当时所谓的“眼科”设备,只有一张视力表、一支手电筒和一台最简单的眼底镜,可以说非常简陋。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眼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在眼科显微手术技术、基础研究体系、眼库建设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代际差”。国外用“洋枪洋炮”,我们还在用“大刀长矛”。这种差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因此,我决心不仅要引进技术,更要改进理念、建立我们自己的科研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
记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您后来都做了哪些工作?
谢立信:做了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1989年,我带着干粮和助手,到苏州眼科医疗器械厂举办全国眼科显微镜手术培训班无偿授课,工作量巨大,先后对国内27个省(区市)的1000余名眼科医生进行了眼前节显微手术的培训。后来这些“火种”落地生根,让角膜移植和眼前节显微技术在中华大地上遍地开花。再比如,我推动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眼库,推动角膜捐献。这些工作非常艰辛。但看到越来越多的医生掌握新技术,越来越多的角膜盲患者因为角膜捐献重见光明,我就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
1991年,在山东省、青岛市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我们在青岛创立了山东省眼科研究所。起步时研究所只有2名医生、1名护士和25万元启动资金,但我们有一个清晰的蓝图:既要有一流的临床服务能力,更要有自主研发创新能力。
角膜移植从“经验判断”走向“精准量化”
记者:1989年,您的成果获得眼科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后来,您又获得多项国家和省部级奖励。这些获奖项目都围绕哪些研究主题?
谢立信:这些项目看似独立,实则围绕一条主线:解决角膜病临床诊治中的关键理论和技术瓶颈。
1989年获奖的“穿透性角膜移植术后角膜植片内皮细胞功能失代偿的研究”项目,核心是建立了活体角膜内皮细胞功能评估体系,提出了“活性密度”新标准。角膜移植手术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体角膜内皮的活性。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学术界对如何准确评估角膜内皮功能、如何判定供体角膜是否适合移植,缺乏统一标准。我们团队通过对大量角膜内皮显微镜图像的量化分析,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角膜内皮细胞功能失代偿的临床早期诊断标准”,并创新性地提出了“供体角膜活性密度”这一全新概念和判定标准。
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让角膜移植从“经验判断”走向了“精准量化”。这之后,医生可以像查血常规一样,通过客观指标预测手术成功率。这也标志着我们在角膜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11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的“感染性角膜病创新理论及其技术应用”项目聚焦感染性角膜病,主要解决我们长期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国角膜盲的主要病因是什么?最佳治疗方案是什么?为此,我们牵头组织开展针对全国10省市、20万人的角膜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次大规模调查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真菌感染是中国感染性角膜病致盲的首位原因,这与欧美国家以细菌和病毒为主的情况截然不同。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不同真菌菌丝在角膜内生长方式不同这一现象。基于此,我们提出“早期板层角膜移植治疗真菌性角膜炎”这一全新理念,将一次手术成功率提高到93%以上。这个中国方案改写了国际角膜病诊疗指南,被收录进权威专著《角膜》(Cornea)。
记者:在破解角膜病发病原理的基础上,您又如何解决角膜供应不足的问题?
谢立信:近年来,我们在角膜替代材料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理论研究再深入,临床技术再高明,都绕不过一个根本难题:角膜供体严重短缺。我国有近400万角膜盲患者,每年却只能进行约1万例角膜移植手术,供需矛盾极其尖锐。
在此背景下,我们团队将重心转向角膜替代材料研发。这项工作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生物工程角膜,我们提出了“基于胶体渗透压调节的脱细胞新理论”,研制出保留天然角膜结构同时去除免疫原性的猪角膜基质。二是完全人工合成角膜,我们与工程团队合作,攻克了镜柱微米级加工、生物相容性等难题,研制出适合中国人眼结构的国产人工角膜,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这些材料创新不是要完全取代人体角膜,而是构建了“人体捐献角膜—生物工程角膜—人工角膜”的梯次化解决方案,让不同病情的患者都有复明的可能。
这几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都对应着我国角膜病诊疗能力的跃升,体现了从基础理论到流行病学,再到产品研发的递进关系,推动我国角膜病诊疗从依赖经验走向科学循证,从依赖捐献走向自主研发。
记者:您一直在眼科科研领域勇闯“无人区”,科研成果造福了众多患者。您认为是什么让您取得了这些成绩?
谢立信:我的体会是,必须紧紧抓住“临床需求”这个牛鼻子。所有研究的起点都是临床中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在临床上我们发现,真菌性角膜炎手术容易复发。为了弄清楚这背后的原因,我们回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不同菌丝的不同生长方式,这才诞生了新的手术理论。再比如,看到那么多患者在等待角膜供体的过程中失明,才“逼着”我们下决心攻关人工角膜和生物工程角膜。
闯荡“无人区”还需要学科交叉的视野和勇气。人工角膜的镜柱,需要在绿豆大小的材料上进行微米级精密加工,这离不开与材料科学、精密制造专家的深度合作。基因治疗、干细胞研究更是如此。
记者:当前眼科学领域的发展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谢立信:当前眼科学面临两大趋势:一是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基因编辑、干细胞、人工智能、新型生物材料等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眼科诊疗的模式;二是转化医学周期大大缩短,基础研究的突破能更快地走向临床应用。
我们面临巨大机遇。我国有庞大的患者群体和临床资源,有日益强大的工程技术和制造能力,在人工智能应用、高端医疗器械研发等方面有机会实现弯道超车。
挑战同样严峻:一是在一些高端检查设备、特殊耗材的核心部件研发方面依旧存在瓶颈;二是顶尖复合型人才短缺,既懂临床又深谙前沿科技的领军人才不足;三是仍需改革科研评价体系,使其更有利于鼓励源头创新和解决真问题。
为此,需要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改革人才评价机制,真正营造让人才潜心研究和开展交叉合作的环境。
教学可让经验积累产生乘数效应
记者:您已在角膜病防治领域耕耘了60年。是什么让您保持如此长久的热情?
谢立信:我的动力源头很简单,就是患者的需求和患者重获光明时的笑容。每当完成一例高风险手术,看到患者揭开纱布那一刻的眼神,我所有的疲惫和压力都烟消云散。这种直接的、正向的反馈,是医学研究独特的魅力。
记者:您曾说过,等您老了,所有头衔都可以不要,只保留教师身份。为什么这么说?
谢立信:我珍视教师身份,是因为我深知,一个人的技术再高,能救治的患者也是有限的。但通过教学,一个人的影响可以指数级增长。如果你培养出十个、一百个优秀的医生,他们又能培养更多的人。我的知识和经验,来自前辈的教导,也离不开患者的信任,我有责任将其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下一代。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培养了500多名硕士、博士。他们中有的已经成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有的在偏远地区建立了高水平的眼科中心。看到学生们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专家,在各地为眼健康事业奋斗,那种喜悦和成就感,比我自己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或者完成一台高难度手术还要强烈。所以,“院士”“院长”是阶段性的社会角色,而“老师”是终身的。
记者:在您看来,眼科领域应如何吸引更多优秀年轻人,并让他们脱颖而出?
谢立信:第一,要展现眼科的价值和魅力。它不仅是“开刀治病”,更是融合了精密手术、前沿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的“高精尖”领域,是守护人类最重要感官——视觉的崇高事业。第二,要搭建好的平台,给予年轻人施展才华的机会,在重大项目中设立青年骨干比例,让他们在实践中快速成长。第三,要改革评价机制,保障年轻研究人员的研究时间,认可他们的独立贡献,在成果署名、奖励申报上要规矩严明,让实干者得实惠。最后,要营造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文化,允许年轻人在不确定中探索新方向。
记者:在培养学生时,您最看重他们什么品质?多年从教给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谢立信:我最看重两点:一是“德”,医学是仁术,要有高尚的医德和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二是“创新能力”,科研不是简单重复老师的工作,而要鼓励学生质疑、探索,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
收获是丰硕的。我们培养的很多学生已成为国内各大医院的学科骨干或带头人。更让我欣慰的是,一个老中青结合、富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团队已经形成,这是我能力最大的延伸和我收获的最大财富。
记者:您对中国眼科的未来,还有哪些希望?
谢立信:我已经八十三岁了,但我的心态和六十年前第一次拿起手术刀时没有太大不同。每天早晨走进医院,看到候诊区坐满患者,我就感到一种责任和动力。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站在手术台前、实验室里、讲台上。
如果要说希望,我有三个。一是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引领。比如,在角膜再生医学、疑难角膜病的基因治疗方面,做出“从0到1”的原创贡献。二是建成国内一流的眼科中心。这个“一流”,不仅看规模,更要看能否持续产出改变临床实践的重大成果,能否制定国际认可的诊疗指南。最后,我还希望看到我的学生们在各自的领域实现超越,把角膜病治疗事业的火种传得更远。
医学的发展就像一场接力赛,我很庆幸自己跑了很长的一棒。现在,接力棒正在传递给年轻一代。我相信,在他们的手中,中国必将从“眼科大国”迈向“眼科强国”,为全人类的眼健康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致青年科技人才
对于年轻人,我想说,首先,要找到真正的兴趣点。做研究,不要追热点、追“帽子”,而是要找到那个让你心甘情愿为之熬夜、为之痴迷的科学问题。其次,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我们研发生物工程角膜,从实验到首例手术成功,用了近十年。重大创新往往需要坐冷板凳。最后,要建立“临床—科研”双向通道,在临床中发现问题,用科研解决问题,再让成果回馈临床,这个闭环能不断带来成就感和新问题,让研究“活”起来。
——谢立信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